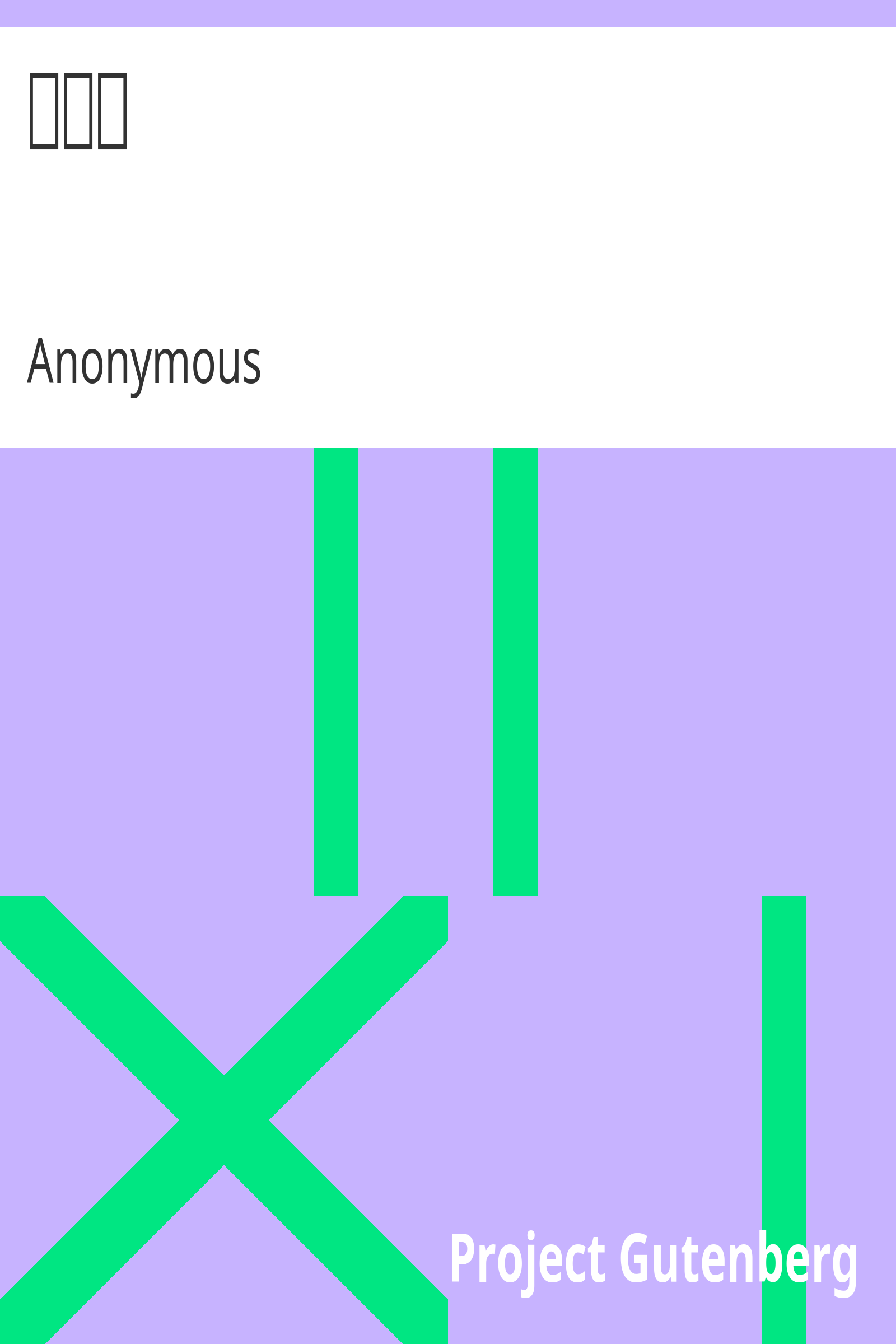山水情
Play Sample
第十八回 金昆聯榜錦衣旋
石室思歸上,仙攜出洞天。萬重滄海渡如煙。頃刻燕京,相遇至親緣。鏖戰爭先捷,錦衣兩兩旋。門庭裘馬自翩翩。知己傾懷,丹藥救嬋娟。 右調寄《南柯子》 卻說那衛旭霞在雲林夫人宮中宴罷,紫陽引歸石室,一連住了五、六晝夜。一日,心中焦躁起來,乃對張紫陽道:「蒙大仙渡凡子到來避災脫厄,今已五、六日,不識災星曾過也未?欲往京都會試,去遲有誤功名。請問大仙,歸期定在何日?」 紫陽道:「目下你的災星已退,榮華漸至。今試期將迫,若到了家裡起身,一時去不及了。莫若一徑送你至京,會試了歸家,倒覺便捷。」旭霞道:「承大仙美愛,是極妙的。但乏盤費怎處?」紫陽道:「我護你去,自有安放之法,不消憂慮盤費的。我且問你,昔日在雨花台授你丹藥,如今回去要用著他了呢。」 旭霞聽了這句話,驚訝呆想一回,乃道:「凡子在仙界這幾日,竟不曉得竟是紫陽大仙。」連忙跪下拜求道:「向日蒙賜金丹,豈敢有違教命?至今牢佩在身。只這四句仙機,難於解悟。未審大仙肯明示否?」紫陽道:「那個玄機,你的姻緣該成就時,自當顯然應驗,不必先曉得的。我今原備小舟在山麓水涯,渡你到京。」旭霞心中惶惑,暗想道:「倘然到京時,並無親戚故舊,弄得進退兩難,何以為計?」紫陽見他遲疑,乃道:「我仙家之法,是隨機變化的,目下難以明言。我引你到的時節,自有奇遇,不必細究。」旭霞聽罷,遂拜謝了。 紫陽仍化作舟人模樣,引了旭霞,紆迴曲折的走出山坡。將近水之際,真有一葉泊於岸邊。紫陽說請登舟,旭霞心裡想道:「怎的又不是前日來時泊船的所在了?」更遠遠一望,但見茫洋大海,波浪滔天,忽然害怕起來,乃問張紫陽道:「莫非要從此海面渡去?」紫陽道:「正是。」旭霞戰兢兢的道:「若如此,必得大舟方好。」 紫陽道:「我這裡艨艟巨艦是用不著的,只有那小小輕舟,倒覺便捷。你不消害怕,下船去,原是前日渡來時一般的睡在艙裡,包你穩便到京。」旭霞聽了,只得顫巍巍心驚膽戰的下了船;遵著紫陽之言,睡於艙內。那紫陽如前替他冒好了,扯起雲帆,如飛的去了。正是: 仙帆破浪乘風去,弱水蓬萊頃刻過。 看官們,你道張紫陽渡衛旭霞至仙界去,好不詫異,才住下五、六日,凡間已是三足年。到京時,誰知已是下科,那個吉彥霄已發甲去了;杜卿雲也鄉薦了,帶了鷓兒,來京等會試;作寓於蓮子衚衕。其時二月中旬,卿雲在寓無聊,偶然假寐榻上,叫鷓兒在外看門。 那張紫陽競將衛旭霞從空負至門首,對旭霞道:「這便是你安身會試處了。」旭霞此時,正驚疑未定,回頭一看那張紫陽,忽不見了,心裡暗想道:「怎的幾千里之遙,如此迅速,真個是飛仙,變幻莫測。但是他許我有安頓之處,如何並不指示一言,竟自去了?」 躊躕四顧,惶惶失色。不意安睛一看,只見一家門前,坐一個人在那裡打盹。近前細看,竟像自己家僮鷓兒的模樣。旭霞想道:「這裡既是京師,去蘇州有三千里路,緣何我家鷓兒得到此間?但面貌何故十分廝像?」欲待要叫一聲「鷓兒」,又恐不是,便覺不好,只得走近門首,觀其動靜。 誰知那鷓兒一個瞌睡撞在門上,撞痛了頭皮,這才醒來。張眼一看,只見那門首立個人兒,儼然家主模樣,驀地吃驚,如拾絕世異寶,不覺亂跳亂嚷,急奔進去,叫:「杜相公,我家大相公在外邊!」卿雲道:「青天白日,又來見鬼!」鷓兒道:「真個是大相公!杜相公可出去看便是。」 卿雲見鷓兒如此,遂急忙走出,看時,實是旭霞站在那裡,將要上前開口。豈料旭霞始初見了鷓兒,還著些狐疑;至此見了卿雲,遂想著紫陽所囑「到時自有奇遇」之言,更不疑惑,便信口叫:「卿雲表兄,你如何在這裡?」卿雲亦問道:「表弟,你一向在何處?」旭霞道:「做表弟的幾乎死於他鄉,不想今日在這裡得見親人之面!」卿雲道:「這也奇怪得緊!人人道你不知漂流何處,今日緣何知我在此,得以尋來?」遂同旭霞進去相見過。那個鷓兒也不免來家主前慇懃一番,旭霞亦不免撫憐他幾句。 卿雲道:「表弟,這三足年虧你在那裡過日?」旭霞聽他說了「三足年」,呆了。卿雲見他如此光景,問道:「表弟,你一向起居如何?難道年、月、日、時也不省得的?」旭霞道:「說起來甚是可駭。我為本山鳳來儀家誘去,強逼成婚。餘心不願,坐了一夜,黎明遁出他家。本欲渡湖到表兄家躲避,豈知是早航船尚未出來,見一白頭老翁,泊舟岸側,弟招而登之。他把船艙冒好,教我睡在裡邊。弟因隔夜通宵不曾合眼,覺得神思疲倦,竟爾睡去。不知不覺,被他渡至一僻幻之處,泊舟上岸,到那深谷碧雲中住下。後復引至一萬仞山椒上邊什麼雲林夫人宮中去,有無數娉婷仙女在此,遂召弟進去,賜宴賦詩。後復引歸石室。據他道,我這時有難,渡去避脫。目今災星已退,試期已迫,故渡我到京。然在山中盤桓,只得六日耳,緣何表兄方才說三足年?」 卿雲道:「你若不信,待我細細述與你聽。目今這會試,不是老弟發解後之春闈,乃已隔了三年,是下科了。且我今為何在京?因去秋鄉試僥倖了,故在此挨候入場,豈料得遇表弟作伴。」旭霞道:「有這等事?還道是我那科的會試耳!如此說起來,表兄亦是個春元了,恭喜恭喜!但願我和表兄兩人,邀天之幸,同登金榜便好。」卿雲道:「便是。」 旭霞又問道:「那個吉彥霄如今如何?」卿雲道:「他己是上科發甲,入過詞林。邇來丁了父艱,回在家裡。他三年前更有一段美意,為著表弟。不料你不見了,遂爾中止。」旭霞道:「什麼事情?」卿雲道:「是年小春中旬,我同他支硎去看楓葉,偶有興同到那尼庵裡去,望望了凡。誰料適有崑山鄉宦人家的老夫人領了小姐,在庵做預修。那個老夫人是彥霄的嫡親姑娘,叫他進去相見過。出來返棹時,在路上談及他們這些衷曲。他的表妹閨字叫做素瓊。」 旭霞慌忙問道:「這素瓊便怎麼呢?」卿雲道:「彥霄知表弟尚在未娶,欲為執柯。我實歡喜無任,著實從臾他幾句。他便特至崑山與姑娘說了,竟是一諾無辭,遂寫年庚付與。彥霄持歸,即到舍來,轉叫我送到貴山,恰恰是表弟做新聞的時候。詢之鷓兒,曉得了這些情由,遂去拜見鳳老。他把始末根由細細述與我聽,道這節事體,都是那花遇春畫的計。這日不免埋怨著他,他也似表弟一般逃走了。此後我歸來回覆了彥霄,即差人四下找尋表弟,沒有尋處。這時真正急得家父家母日日寢食不安。又憐著鷓兒在家,孤形弔影,命我到山去,將宅子封鎖好了,煩地鄰看守過,隨領尊使來我家住下的。」 旭霞聽了那番說話,道是:「這樣好機會,當面錯過了。今已過三載,諒必作他人配合了。」不覺放命的捶胸跌腳,一急一氣,竟自目瞑口歪的死了去。倒嚇得卿雲,鷓兒面如土色,亂吼亂叫一番,才得氣息懨懨的醒轉來。 卿雲道:「表弟豈不聞『書中有女顏如玉』?若是命裡該娶佳人,不用心去求,無意中竟是得了如花似玉的;倘命中該配丑婦,隨你著意揀選,那裡有美貌的到你?我道還該看淡些兒,何必如此著相?」旭霞道:「這也不是為他。只恨著這花遇春狗才,算這樣事來,弄得七顛八倒,不惟負了彥霄兄之美意,更兼害了那鳳小姐的終身,於心何忍!」卿雲道:「那個花遇春,當時不過攛掇成了,要賺些花紅錢鈔,誰料表弟如此執性,弄出這大風波來。去冬被尊使在劉御使案下叫喊了,責過二十板,擬杖在獄,等候表弟著落定罪。」 旭霞又聽了這一席話,愈覺希奇,不免細細查問卿云。卿雲遂把鷓兒陰告遇官並瑞珠死信,細細述與旭霞聽了。旭霞乃贊歎道:「不料這鷓兒蠢然一物,倒有一片義心!那個花遇春邪謀詭計,害了鳳家,也該受罪一番。但是那個瑞珠小姐,為了我含愧而死,歸去時必要拜祭他一番,以蓋前愆。」卿雲道:「這也是表弟的好心,是理上必該行的。」說罷,叫鷓兒出去買辦。收拾酒肴,與旭霞壓驚遣悶,不一時,掇來擺於桌上。 兩人飲過一回,卿雲乃道:「表弟在仙家飲了瓊漿玉液,只怕凡間之味,怕上口了。」旭霞道:「表兄說那裡話來!若是今日相遇不著,就是一飲一酌,望那一家去設處?」卿雲道:「正是!這個機緣來得奇怪異常,連我也還道在夢中哩!」又飲過幾杯,天色已晚,吃過些飯食,收拾畢,都去睡了,正是: 三秋離別重相見,萬種風波一刻頃。 到得明早,旭霞只等卿雲熟睡,那邊先穿了衣服起來,坐在窗邊,袖中取出畫扇攤開,對了素瓊之面,哭一回,歎一回;想到傷心之際,幾乎又死了。 正在癡思呆想,恰好卿雲起身下牀來,只得袖過,拭乾淚眼,乃對卿雲道:「表兄也起身了麼?」卿雲道:「正是。心中欣幸,不覺十分睡著了些。」旭霞道:「表兄欣幸恁的?」卿雲道:「我與表弟別離三載,頃刻之間,原得同堂相敘,聯牀夜話,縱使鐵石人兒,也不免快活!」 乃歎口氣道:「弟之承母舅、表兄見愛,真正視為己子、胞弟,並無異情。不知何日報答此恩!」卿雲道:「試期甚邇,表弟之才藝,雖非不常者比,然三日不禪,手生荊棘,當著實研窮一番,進場時博得個紗帽籠頭,回去盡有許多得意事兒,所以輕覷不得的呢!」旭霞道:「承表兄金玉之言。」說罷,兩人各自的鑽研文史,日去夜來,無少間斷。 直至三月初三,已是開南選之期,旭霞同了卿雲連進三場,幸得文章俱中試官,並登黃榜。候殿試過,卿雲授了戶部主事,旭霞授了嘉興司李,榮歸故里。正是。 他鄉重遇別離親,共躍龍門拜紫宸。 脫卻白袍更衣錦,榮歸駭霎又驚神。卻說杜老夫婦二人,為著卿雲到京會試,因是獨養愛子,日日懸念不忘;後來見得報過了,是一天之喜;更是衛旭霞外甥忽然間也來報中,無不錯愕喜欣。吉彥霄曉得了,更加快活,親到門來詢問賀過。 杜老夫婦在家商量:「他們兩個回來,要備酒邀賓做興頭事。」正說得熱鬧之際,只見門外那山鷓兒得意揚揚的進來,啟口道:「太老爺,小奴快活得緊!夢裡也不想我家主也到京中來會試,中了進士,今同大老爺一起歸來。」杜老道:「如今在那裡?」鷓兒道:「船歇在葑門外靈官廟前。兩個家主叫小奴先歸,說向老太爺道:快些收拾家裡,喚齊樂人、傘夫、旗手,轎馬迎接。」 杜老聽了,不覺鼓掌踴躍,連忙進去,差人去喚齊役從。支值停當,喚鷓兒領出城去,迎上岸來。不一時,到了門首,真個熱鬧之極。有一曲《黃鶯兒)為證: 雙貴錦衣旋,鬧街坊,鼓樂闐。三簷蓋傘隨風轉。繡鞍兒,色鮮;藍旗兒,粲然。摩肩擦背人爭羨,賽登仙。親年未老,及第樂無邊。 且說杜老夫婦兩個,打發了人從出門去,遂歡天喜地,各自換了鮮明色服,走到廳上觀望。只聽得外面人聲喧沸,那表兄弟兩個,紗帽籠頭,腰銀耀目的走進門來。卿雲先在門前拜家堂祖先,立起身來,同旭霞步至廳中,一同拜見了杜老夫婦,各自卸了公服,走到裡面去。一家至戚,團團坐了,飲酒敘談。 卿雲將京中遇著旭霞的情由,述過一番。杜老亦備言不見了外甥之後寢食不忘的思想。旭霞亦將到仙家之事,從頭至尾。說與母舅、舅母聽過。那杜老夫婦二人聞之,也道奇異,乃歎息道:「賢甥遇仙而去,雖絕世美談,但漂流三載,弄得家裡零零落落。今喜得仙人復渡你到京,得以成就功名回來,萬分之幸。目下當歸故里去,耀祖榮宗一番;然後尋一頭親事成了到任,乃至緊之事。切不可再有執滯,誤人家女子了。」 旭霞道:「母舅這番教訓,愚甥焉敢有違?但婚姻之事,雖云『不孝有三,無後為大』,就目下論之,稍可遲緩。甥回去時,先要擇吉行了葬親事,然後為此。」杜老道:「這也是。」當時傳杯換盞,暢飲幾巡。恰好抵暮了,打點旭霞到書房中去睡過。卿雲也進房去了,他夫妻二入闊別了幾時,又且榮貴雙全,畢竟各自暢懷,與平日之情興,自然加倍不同的。正是: 名成博得家庭樂,不比蘇秦下第時。 卻說這吉彥霄是夜曉得他兩個榮歸了,渴欲會晤,竟自清早起來,打了轎,一徑到卿雲家來。恰好那表兄弟二人,正在那裡打點,要到彥霄處謁拜。使者進來通報了,兩個連忙出門,迎接進去。各自揖過坐定,敘過寒溫一番,彥霄向旭霞道:「誰想年兄三載萍漂,原得與令表兄同登金榜,錦還故里;親戚朋友,復爾相敘,話舊談新,豈非吉人天相!」旭霞道:「弟於三年前,不料隨犯顛沛,幾乎死於他方,不得相見故人。」彥霄道:「敢問年兄,羈跡何處?請道其詳。」 旭霞乃將前事,曲曲折折,述與彥霄聽了,又道:「前者家表兄道及年兄曾欲為弟執柯,豈期吝緣。有負雅愛,至今心實不安。」彥霄道:「這是家表妹沒福做夫人也!」旭霞聽了,道是素瓊已經適人,不覺呆坐椅上,絕口無言。卿雲見他如此光景,乃替他問道:「如今令表妹曾出閣否?」彥霄道:「不要說起,也是一樁極古怪的事。」 旭霞驚問道:「什麼古怪呢?」彥霄道:「小弟自從那日聞兄遁跡之信,回覆了家姑娘,即北上了。直至丁艱返舍,乃知前年有個詹鄉宦家卜吉了,將及送禮。家表妹忽然生一急症,暗啞不能言,延醫獻神,無所不至,究不能愈。」旭霞又驚問道:「莫非令表妹蘭摧玉折了?」彥霄道:「這也倒不曾,竟成一個痼疾,因此詹家就中止了。」旭霞聽得中止之言,心裡想道:「雖則生病,幸而還未曾適人,猶可稍慰萬一。」不覺失聲道:「這也還好!」 彥霄又道:「我聽見家姑娘說,病雖淹留日久,喜得飲食如舊,容顏不減。若得醫他開口一言,依然是個好人了。近日又有一新奇之說,家姑娘因女兒生了此疾,鎮日切切愁煩,恍恍惚惚。偶一夜間睡去,夢見一個道人來對他說:『你家女兒生病,可要醫好他麼?』家姑娘道:『怎的不要醫好?』那道人道:『就要醫好,也不難。我四句詩詞在這裡,可以醫好。念與你記了,寫來貼於門首,自然有人來醫。』家姑娘夢中聽熟了,覺來遂寫貼外邊,後面又增上一行:若有人來醫好小姐者,即送酬金壹百兩。」卿雲、旭霞兩個齊聲問道:「這詩,年兄可記得麼?」彥霄道:「怎不記得?」乃念道: 九日秘藏丹藥,雲頭一段良緣。 舍外無人幻合,攜來素口安痊。 旭霞聽彥霄念畢,倒嚇得魂飛魄散。一頭裂開衣帶,取這丹藥出來;一頭向彥霄道:「世間不信有這樣奇事!難道令姑娘的夢正合著小弟仙人所授的金丹秘語?」彥霄吃驚問道:「年兄有甚仙授金丹秘言?」旭霞道:「若但說,盟兄怎的肯信?待小弟與兄看。」便啟金丹紙包,付與彥霄。 彥霄仔細著眼,錯愕一回,授與卿雲看道:「這也真正奇怪!若是旭霞兄轉了身,就道是寫來哄小弟了。這是家表妹病體當愈,旭霞兄這頭姻事原有可成之機!」卿雲乃道:「怎的表弟在京再不見說起,今日忽然拿出來,又是暗合他人之夢的?莫非在仙家住了三載,亦有了仙術,一時造來哄我們?」旭霞道:「表兄休得取笑!」彥霄道:「敢問旭霞兄,這丹是何等仙人授你的?」 旭霞遂將三年前太白托夢尋仙授藥之說,述與彥霄。卿雲聽過,兩人各自驚駭。彥霄道:「既如此,是天付的姻緣了。我明日就將這丹去,即與兄述這一番奇話,與家姑娘、表妹兩個聽,必要撮合這頭親事的了。」旭霞道:「若得如此,弟一生志願足矣。」 彥霄欲起身告別,卿雲道:「今日承兄先施,一定要屈留尊駕,以敘闊別之衷,兼為家表弟作賀。」彥霄道:「既蒙吾兄雅愛,諒不得卻,只是有費兵廚,怎處?」卿雲乃拱彥霄到園亭中去坐下,教旭霞陪著,自己進去吩咐支值。 不一時,治就佳餚美酒,將來囉列亭中,三人笑談暢飲,觥籌交錯。一回,彥霄忽凝神定睛的思想道:「卿雲兄,弟在這裡細想,那四句仙機預藏得巧。」旭霞、卿雲接口道:「怎見得呢?」彥霄道,「依鄙意解起來,奇異得緊!第一句『九日』,是個『旭』字;第二句『雲頭一段』,是個『霞』字。這顯然是衛兄的尊甫了。那第三句『舍外無人』,豈非是個『吉』字,恰好合著小弟賤姓,又是我今日來談起這事。那第四句『素口安痊』,家表妹閨字叫做素瓊,又是個口病,明明裡說小弟將此丹去與家表妹吃了,就安痊了。這豈不是仙機預藏得幻妙麼?」 旭霞聽了,不覺手舞足蹈,說道:「小弟得此三年,不在心上,今事機湊合,且有彥霄兄一番剖訣,真神仙能發神仙秘矣!若得仗年兄在令姑娘面前亦如此解說一番,撮合了小弟百年姻眷,此恩此德,至死不忘!」那表兄弟兩個,又輪流敬過彥霄幾杯,共談些世事,彥霄起身作別而去了。 卻說那杜卿雲、旭霞到得來日,就去答拜了彥霄;回家於合郡中鄉紳、任官,也都去拜謁了。旭霞遂收拾榮歸故里,此時就有許多俊僕來投靠,隨意收用幾擋,喚了極大的船隻,由胥口出湖,一帆風順的回山去了。以後不知姻緣可就?且聽下回分解。 敘舊述話,色色摹神。衛生到京,吉生說夢,令人於此有羽化飄飄之想。 摹寫新進士行動,窮措大亦為解顏。
第十九回 櫻桃口吞丹除啞症
繹唇已作三緘口,默默無言久,鬢雲不理罷妝紅,帷擁衾裯,聽暮鼓晨鍾。金丹吞卻字如蟻,詢出情人意。萱親喜氣上雙眉,囑語冰人,毋誤鵲橋時。
右調寄《虞美人》
卻說老夫人為著素瓊愛女生了這個啞疾,將及三載,延醫服藥,不能痊可。自從得了這夢,將來寫於門首;又托彥霄姪兒往蘇州去察訪。將及幾個月,並無應驗。正在那裡暗苦怨命,窮思極想,忽聽得簷頭鵲噪幾聲,乃歎道,「自古來燈花生燄鵲聲喧,必是佳兆,難道偏是我家不准的?如今不免到門首去探望探望看。」乃喚了碧霞,同到外面;倚著門兒,立在那邊,呆望半日。
將欲轉身進去,忽見吉彥霄走進門來,劈面撞著,說道:「姑娘,為何在此倚門而望?」老夫人道:「我正在家想念你來,因鵲噪簷前,故特走出來觀望,不料果應其兆,得賢姪到來。」同了一齊走到廳上。彥霄作過揖,坐了。老夫人叫碧霞進去點茶來。彥霄道:「姑娘邇來身子康健麼?」老夫人道:「目下為著你表妹,鎮日憂愁,飯食也減常了。只怕死在目前目後矣!」
彥霄道:「姑娘怎說這樣話來?表妹可能說一言半語否?」老夫人道:「因為再不肯開口,故此心焦。」彥霄道:「姑娘不必愁煩,好在即日了。」老夫人道:「何以見得?」彥霄道:「姪兒記這姑娘夢中的詩句回去,豈料一故友在京會試榮歸,去拜望他,無意中說起,將這四句詩念與他聽。彼一時驚駭無已,忙向衣帶中取出一丸丹藥來,付與姪兒。啟看好不古怪!裡面竟是一樣的四句詩,寫在紙上。此時姪兒欣喜無任,乃細細查問,道三年前太白金星化一白頭老人托夢,教他尋仙,指示姻緣,遂於本山雨花台得遇一個仙人,授他丹藥一丸,秘語四句。他恐遺望了,將其語寫於藥包上,時常帶在身邊。今適姪兒說著了,即以此藥付我,拿來醫表妹的病。」
老夫人頓開喜顏道:「不信我夢得如此奇驗!若醫好了,當以百金謝他。」彥霄道:「這個人不要銀子的。」老夫人道:「他是何等人物,不要銀子?」彥霄道:「就是向年姪兒與他做媒的人兒,如今已中過進士了。他說若醫好了,要求表妹為配。」
老夫人聽了這話,乃驚駭道:「你說這個衛生不見了,如何忽然又得中進士?」彥霄遂將他遇仙渡去之說,述了一遍,又道:「更有一樁奇怪情由在內。我道今日吃了這丹,必然就能開口。」老夫人道:「又是恁般奇怪情由?」彥霄遂將所解詩中暗謎,述與老夫人聽了;即於袖中取出這丹,付與姑娘。
老夫人歡天喜地的接了,乃道:「依姪兒如此說來,這樣湊巧,暗合仙機,必竟是天緣了。若得痊癒了,當依允便罷。」說畢,同彥霄到內室中教他坐下,一面吩咐收拾點心;一面慌慌忙忙的將那丸藥進房去,叫春桃化與素瓊吃。老夫人立在牀邊,看了一回,不見動靜,對春桃道:「你替小姐蓋好了,伴在那邊,待他睡一覺兒看。我到外邊去支值吉老爺吃了點心,就來看也。」徑自走出房去了。正是:
金丹投卻嬌兒口,指望能言快霍然。
卻說那春桃聽了吩咐,替小姐蓋好了,立在牀邊,作伴呆看。但見素瓊真個□□的睡去了。此時春桃在那裡暗想道:「我自從小姐得了此疾,三年不言,倒害得我寂寞難過。今日那吉家老爺,與衛生傳遞仙丹到來。若他們兩個三生有幸,真個靈驗,使小姐好了,完就姻緣之事,或者連我也摯帶摯帶,可不是一樁極快暢的美事?但恐怕好事多艱,蒼天怎肯把一個現成夫人,唾手付與我家小姐?」
正想間,只見牀上番個身兒醒來,忽然作聲長歎。春桃覺得詫異,乃悄悄走近牀去,叫一聲:「小姐。」素瓊竟是慢慢的發言道:「春桃,我口渴得緊,快快取茶來吃。」春桃聽見他開口說話,一時倒歡喜得遍身麻木了,不及答應,拍手拍腳的笑到外邊去。
那老夫人陪彥霄在書房裡飲酒,聽見了,忙喚春桃進去,問他為何如此歡笑。春桃道:「小姐竟開口說話了。」老夫人與吉彥霄聽了,齊聲道:「有這樣奇事,如此靈驗?真個是仙丹了!」彥霄乃對老夫人道:「姑娘,你進去看來。」老夫人遂喚春桃,拿了一壺好茶,口裡連連念佛,走進房去,乃道:「我兒,你好了麼?」
素瓊懶垂垂的道:「母親,不知因甚緣故,方才睡去,夢見一白鬚老翁向女兒說道:『若不是我取你司言之官去,幾乎鳳入雞群了。如今是你成就之時,原還了你罷。』說完,竟將一個舌頭推入我口中,把頭來一拍,飄然而去了。醒轉來,覺得身體輕鬆,舌根氣軟,漸漸能言。但有些口渴,故叫春桃出來取茶吃。」
老夫人此時見他痊癒如故,欣欣然的接春桃的茶來,篩一杯兒,與素瓊飲畢,乃道:「你患了此症三年,倒害得做娘的幾乎愁死。如今喜得蒼天眷佑,暗遣吉家表兄為你覓得一丸仙丹到來,方才我化與你服過,得以如此。不然,怎能夠脫體?」素瓊乃驚訝道:「吉家表兄何處覓來的,靈驗若此?」老夫人道:「你的病才好得,說起來甚是話長,恐傷了你神思,又弄出事來。停二日兒對你講罷。」
素瓊道:「母親不妨,須說向女兒知道了,也曉得表兄救我之恩。」老夫人道:「若是你耐煩得,待我述與你聽。」乃道:「我自從你得了病後,不知費了許多煩惱!日夜焦心勞思,寢食不安。今年正月間夜裡睡去,夢一道人,念詩四句,教我寫來貼於門首,自有人來醫驗。我依了他,貼在外邊。又是念與吉家表兄聽了,他便牢記在心;回去時,恰好那了凡的弟子漂流在外,中了進士,榮歸相會時,無意中談起。你道好不古怪!這衛生於三年前曾有太白星托夢,教他尋仙,指示姻緣。果得遇仙,授與金丹一粒,隱謎四句,寫在包內,時刻佩帶在身邊的。見你表兄念我夢中之句,他聽了,道是與他仙人這四句不差一字的,乃欣然出諸衣帶中,慨付與他。今日親自持來的,現今還在外邊。」
素瓊道:「原來這個緣故。但方才母親說夢中這四句詩,可記得了?」老夫人道:「適間這紙包內有得寫在上邊,春桃可拿來與小姐看。」春桃連忙在桌上去取來,付與素瓊。
素瓊接來一看,袖過了。又問道:「那個了凡的弟子,記得前年說他漂流在外,生死難期了,今日何由又得中進士回來?」老夫人道:「說起又是一出奇怪的事。」素瓊乃暗暗驚問道:「什麼奇怪,莫非是他撇了鳳家,隱遁他方,學那蔡邕負義,贅人豪門,如今登第榮歸麼?」
老夫人道:「非也。吉家表兄說他還不曾娶。不見了這三年,你道在那裡?竟是被一個仙人渡去,鎮日與仙童仙女吟詩作賦,取樂了三秋。今因會試期近了,原引他到京。恰好他的一個表兄,也在京中會試,乃得一同登榜回來。更聽見你表兄說,那仙人授的丹、詩,原暗藏姻緣之機在內。如今只等好了,要來求親,原是你表兄做媒。若做得成時,也完卻我心上之事。」
素瓊聽了這番話,覺得心花頓開,但是不好答言,倒是春桃接口道:「依奶奶如此說來,那個衛生,久羈仙界,必有仙風道骨。目今又得發甲榮歸,自然是天下第一福人了。更得這仙丹,恰恰將來醫好我家小姐。若非是天緣,怎能如此湊巧,如此靈驗?若是吉爺肯做媒,奶奶可速速煩他去說,快成了罷,省得那包、趙兩媒婆曉得小姐好了,又來圂帳。」老夫人道:「我出去時,隨即吩咐吉爺,教他歸去時,作速去說便了。」又對素瓊道:「我出去一回,再來看你。春桃,你好好相伴小姐在此,要茶吃,我自出去叫碧霞送進來也。」
那老夫人歡天喜地的出了房門,走到書房裡去,將素瓊言語如故之事,述與彥霄聽了。姑姪二人,互相稱快一回。老夫人乃喚碧霞烹茶進去;復喚柳兒暖一壺酒過來,連連篩與彥霄,說說話話的飲。正是:
一腔煩惱如雲散,頃刻愁容變喜容。
卻說那素瓊聽了母親這番入耳之言,又是春桃這一派從臾,更快暢自己病痊,暗暗歡喜。想了一回,乃對春桃道:「世間有這樣希奇事情!那個衛生,人人揣度他死了,豈料竟在仙家作樂。但不知此說可真否?」春桃道:「只這一丸仙丹,就來得古怪了。也不必疑得。」素瓊道:「我也如此摹擬。想衛生,非謫仙,即降星也。」
春桃道:「或者小姐與他該是夫妻。仙人授丹時,婚姻之數明明指示,定在那邊的了。衛生命中,應遲滯婚姻,恐小姐被他家聘去,故天使生病的生病,漂流的漂流,幻出這些奇境來,敷演過了。目下當成就之時,事事皆湊合攏來了。」素瓊聽得,不覺失聲一笑,乃道:「這個丫頭,又是一個當代的女朱文公了。」
正說話間,老夫人牽掛素瓊,復進來探看一番。恰值天色黑了,叫春桃服事小姐吃了夜膳,支值睡了,到外廂去打點彥霄安置了。
到得天明起來,收拾朝飯吃過,叮囑做媒之事一番。不免謝過幾聲,將些禮物送他。彥霄拜別姑娘,出門而去。正是:
三年啞疾默無言,一遇仙丹遂霍然。
緩啟朱唇忙運舌,徐徐詢出意中緣。
卻說那吉彥霄將這衛旭霞的仙丹,來醫好了素瓊,老夫人情願將這小姐配與旭霞。不知他回去對旭霞說了,幾時來求親,且聽下回分解。
素瓊曉得衛生不死,又復不娶,又復來求親,痼疾便當霍然,不必仙丹到口也。
第二十回 莫逆友撮合締朱陳
隱跡三年遠境,一朝衣錦榮旋。故人敘出鳳家言,躬祭傾觴消愆。葬樞往探姻事,相嘲驚淚如泉。和盤托出扇頭顏,得訂雀屏開選。 右調寄《西江月》 卻說那衛旭霞榮歸故園,真個驚動長圻一帶老少山民,個個喝采。更且平昔的相知故舊,都自拜望。旭霞停過兩日,亦不免各家去登門答謁了。如此你來我往,熱鬧門庭,也可謂榮耀之極。但是到山時,聞得了鳳來儀夫婦二人相繼而亡,心上未免有些慘傷,過意不去,只得備了祭禮,去布奠他夫妻、亡女三人一番。然後請了堪輿,擇日起造墳塋,葬了雙親。諸事理畢,遂思想吉彥霄得仙丹去,不知有效無效,心急如箭,巴不能夠插翅到蘇。 一日,留兩擋親靠的家人,看住了宅子,叫鷓兒隨了,一徑到卿雲家來。少敘片時,即打轎到吉家去,豈知吉彥霄有事到浙中去了。中心怏怏回來,坐於卿雲齋頭,千思萬想的難過。卿雲見他眉攢戚戚,就曉得他去尋彥霄不遇,為著這樁事心急納悶,正未知已有那好消息了。 卿雲此時,要故意作耍他,說道:「表弟可是會不著彥霄兄,在此不快麼?」旭霞道:「正是。」卿雲道:「前者他到崑山一日,歸時即到我家回覆了,到杭州去的。我方才恐表弟著惱,故不敢說。」旭霞聽得「著惱」二字,不覺失色的驚問道:「他來回覆表兄什麼話兒?」卿雲道:「大凡事體,再不可磋跎的。若一失之於先,必要悔之於後。」旭霞道:「怎的呢?」 卿雲道:「彥霄兄將這丹去,與他表妹吃了,頃刻之間,如狂風捲霧,得見青天,痊癒如故了。以後彥霄兄遂啟口說及姻事,豈知那老夫人因前番出庚來哄了他,目下道是用藥神效,感激是感激的,求婚之說執意不肯金諾。其中更有什麼不可言之事,他略露過一句,就縮了口。弟再四查問,他竟不肯說,但酬金百兩幸喜不食言,餘外並無別話了。」 旭霞道:「不信有這樣奇事!小弟與他家有什麼不可言之事?且待彥霄兄回來,與他講。就是一萬銀子,我那個看他在眼裡!若果然不肯與我聯姻,只要他原去尋那張紫陽討丸金丹賠了我,萬事全休。」 卿雲道:「表弟又來說癡話了,仙人豈是容易相值的?昔漢武帝欲尋不死之藥,差無數童男女往三神山去,不知費了許多心思,究竟不知其所終。今表弟也若要他尋仙,覓丹來償你,真個是使渠去大海摸針了。倘彥霄來時,還得委曲些兒,或者還有一線可通之路亦未可知。」旭霞道:「表兄之言,焉敢不聽!但目前憑限只得兩個月了,那有慢工夫去與他歪纏!這便怎處?」 卿雲正在那裡暗笑他,恰好門上人進來報導,「吉老爺到了。」卿雲同了旭霞出去迎接進來。作過揖,坐定,吃了一道茶,彥霄即欲啟口說及做媒事,忽然想著旭霞前番這些癡情,乃道:「待我且說一個謊,哄他一哄,取笑一番,然後說出真情未遲。」 正在那裡凝睛細想,旭霞心中躁急,熬不過,開口乃道:「彥霄兄,平昔相敘,高談闊論,極有興的,今日為何口將言而囁嚅也?」彥霄道:「也沒什麼,只為叨擔了盟兄的仙丹去,不能遂小弟先日之言以報尊命,故爾不敢輕易啟口。」 旭霞嚇得滿身冷汗,戰戰兢兢的道:「方才家表兄說此丹已是奏效的了,更有何事難以顯言。」彥霄道:「丹藥是靈驗甚速的,但是其中更有一段難與兄言之事。」卿雲此時見得彥霄如此光景,乃暗想道:「前日他來對我說時,是允的了。我方才不過是造誑耍他,何故彥霄也是欲言不言,莫非彼家真變卦了?」正在那裡冷覷。 此時旭霞真個急得沒主意了,遂立起身來道:「好歹求盟兄賜教了罷,何可只管含糊?」彥霄道:「家表妹服了仙丹,停過半日,漸漸能言如故。小弟遂不勝之喜,道是盟兄姻緣之事,竟有十分成就之機。豈知他母女兩個,各執一性。弟再三言之,竟不肯出口說一個『允』字。」 卿雲此時也為表弟著急,慌忙問道:「他兩位執恁般性兒?」彥霄道:「不要說起!家姑娘呢,道是從不曾出庚的,前番哄了他,因而不利,生起病來,幾乎害了性命;情願酬金從厚,議婚之說,萬無此理。這時我道,家姑娘不允,倘或家表妹感激仙丹再造,或者倒是情願的,還可於中苦勸玉成,悄地遣春桃進去,做了蜂媒蝶使。誰料他的執性,更甚於為母者。不知有什麼不愜意於兄,怨恨忿忿,堅拒不從。又似不可向人明言者。如此小弟遂怫然返舍,即到卿雲兄處來回覆了,到杭州去的。聞兄今早到舍來,尊駕才出得門,小弟即於此時返舍的,未曾駐足,即來報命。」 旭霞聽了彥霄這一席話,乃心虛了,竟不答言。但覺五臟如裂,汗流髮指,魂飛魄蕩的,暗想道:「那個寡婦不肯,猶可說也。可笑那素瓊小姐,向日我雖題和了那首詩,又不曾明寫某人題扇索和之情,出來獻你的丑。我道不為什麼大過,何竟頓起鐵石心腸,把往日這段愛小生的芳情,一旦付之東流?」想到此境,竟爾不避羞恥的大哭起來。 此時彥霄、卿雲兩個,始初暗裡好笑,見他情癡光景,失聲大笑,哄堂一回。彥霄乃對旭霞道:「年兄何可如此認真!把情懷放淡些兒。」旭霞道:「豈不聞情之所鍾,在我輩耶?」卿雲道:「表弟差了。你與他又不相識,有何鍾情處,也值得如此傷心?」旭霞道:「豈無?」彥霄道:「難道家表妹先與兄彼此識荊的了?」 旭霞道:「不瞞兄說,也曾略略見過一面。既是他執性了,我如今也不肯與他藏羞掩恥了。他道我觸突了他,見棄往日向慕之情。現有他執證在我處,我非泛泛而為之者。即如那個鳳家家資、美女,一旦不受,原是為著他做此負義之事;不然,到手的洞房花燭,何可棄之而逃耶?」 彥霄、卿雲見旭霞說了這些話,又聽見說出「執證」二字來,倒驚呆了半晌。彥霄遂問道:「什麼執證呢?」旭霞此時,正在盛怒之際,就要在袖中取出這把畫扇來與他們看,又恐怕不雅,乃向袖中摸了一回,又停住手。 此時彥霄見他躊躕,暗想:「必竟道是表妹有什麼情詩了。」竟走近身去,一把揪住了旭霞的衣袖,著實一搜,摸著了這扇,拿在手中,與卿雲細細的看。旭霞欲要去奪來藏過,又怕扯壞了,遂停了手,索性讓他們兩個看個真切,自己在廳上踱來踱去的摹腹懊恨。 兩人看罷,各自驚駭。卿雲道:「這個男子,明明是家表弟的樣兒。這個娉婷,想必是令表妹的尊容了。看起這首詩來,自己倡韻,先存炫玉求售的意思在內,也怪不得家表弟奉和自媒。」彥霄是至戚關情的,此時見了,不免有些不樂,又不好見之於詞色,乃略略答言道:「正是。」卿雲又道:「令表妹有此才技,真可稱女中學士了。」 彥霄道:「這樣不由其道、無媒自前的事,那裡算得才技?但若小弟今日不見這柄扇子,他母女執性也不便去強他了;既承旭霞兄不避瓜李之嫌,和盤托出,弟倒丟不得手了。待弟將這把扇子去,在表妹前暴白一下,再與家姑娘說了,促他快快成了姻罷。」旭霞見說要替他促成姻事,頓生歡喜,但聽見要拿這扇去對證,心中又捨不得,乃道:「彥霄兄,扇子拿去不得的。」彥霄道:「若無他原韻去,何以為兄暴白?」遂袖了扇子,起身作別。 兩人送出門時,彥霄又復轉身來對旭霞道:「小弟明日就發棹去了。盟兄可住在令親處,俟候好消息罷。」旭霞喜不自勝。彥霄又扯了卿雲到街心去,附耳低言道:「我始初道是令表弟是個情癡,說個謊來哄他。不道說到後邊,倒露不得真情了。前日所言已允之說,吾兄曾說向令表弟知否?」卿雲道:「不必憂慮。小弟方才亦為哄他,先說令親處不允,已嚇過他一番了,但不十分與兄之言合符,略略大同小異的。」彥霄道:「這個還好,省得令表弟見氣,索性大家不要露出圭角來,到事成之後說明,就無關係了。」說罷,遂拱手而別,上轎去了。正是: 金蘭至戚相嘲戲,惹得情癡淚滿腮。 卻說那表兄弟二人,送了吉彥霄去,轉身進來,卿雲有事到裡面去了,旭霞獨坐空齋,思想尼庵之事,乃嗟歎道:「最可恨者,那花遇春一人耳!我若不是他說計哄騙到鳳來儀家去,做這事體,是年小春中旬,他到庵還受生時節,自然去踐雲仙之約,會晤素瓊小姐。那時便遣雲仙做個蜂媒蝶使,兩下私訂了姻盟,中解歸時,吉彥霄作伐成過了親,亦未可知。何由延挨至今,惹出這許多惡風波來?論這情理上來,真個該千刀萬剮的!」乃捶胸跌足一回,默默無言,臥於榻上。恰好平頭兒請吃點心,遂立起身來,整整衣冠,到裡頭去了。不題。 卻說那吉彥霄回去,把這扇子將來仔細一看,乃恨的道:「世間那起三姑六婆,真是宦家閨閫之蠹,再不差的!好好裡一個千金貞女,被她哄騙到庵去,做出這樣勾當來。更可笑我家姑娘,只得一個女兒,不能防閒他,任他與人詩詞往來,竟自置之不問。如今幸爾大遣這柄扇來與我見了,自然與他隱諱的。若落到別人眼裡,被他播揚出去,怎處?如今且待我暫收在此。到姑娘處,得成了親事,慢還他。倘不允時,倒不便還他,竟自毀碎,以滅其跡,卻不甚好。」遂將扇包好,鎖在匣中。 到得明日,下了船,望崑山進發,不終日間到了。走進門去,與老夫人相見了,乃道:「近日表妹安穩的麼?」老夫人道:「感謝不盡,一好如舊。」彥霄道:「如此極妙。今姪兒特來與他作伐,不識姑娘尊意何如?」老夫人道:「賢姪做媒,難道有什麼差處,不聽你呢?況你表妹原是那衛生的仙丹醫好的,又是一個新進士,只怕他不肯俯就,我這裡再無不允之理。但有一件,賢姪諒來是曉得的:我因年老無依,要入贅倚靠終身的,不識他可願否?」彥霄道:「他也是椿萱都去世的了。若去說時,自然樂從的,但是他赴任之期在即,倘送過聘,就要成親的呢。姑娘也要計議定了,為姪兒的好去回覆。」 老夫人聽了這句話,思想一回,乃道:「待我且去吩咐收拾點心與你吃了,再商量。」說罷,進去吩咐過廚下,即到素瓊房裡去通知了一聲。出來恰好有點心了,喚碧霞掇到書房裡,與彥霄吃過,乃道:「賢姪方才雲就要成親之說,算來也使得的。我方才已曾進去,在你表妹面前通知過一聲,他不答言,想是願的了。你明日回去時,說我們要招贅他,該是女家下聘的。因沒人支值,倒教他從儉送些聘禮過來,然後與他擇吉成親便了。」彥霄道:「姑娘高見,甚是妙極。待姪兒明日歸時,就去促他擇行聘吉期送來。」說罷,又吃過兩壺茶,至夜睡了。 次早起來,梳洗飯後,原請了庚帖,下船歸去。正是: 百年姻眷今朝定,兩下相思一筆勾。 卻說那衛旭霞聽了彥霄吩咐,准准牢住卿雲家裡,望眼將穿,等候回音。正在那裡焦躁,只見鷓兒進來報導:「外邊吉老爺到了。」旭霞欣欣出去,迎接進廳,作揖坐定,喚鷓兒來點茶吃過。彥霄道:「令表兄可在?」旭霞道:「有事他出去了。」遂啟口道:「煩兄大駕,往返長途,弟深抱不安。未審到令姑娘處怎樣委曲鼎言,令表妹處恁般為弟措辭暴白了?」 彥霄道:「小弟此去,先說得家姑娘允了,然後乘間喚侍女春桃,教他傳語,細細與兄代言請罪過。那時將這柄畫扇,授與他拿進去。那侍女依了小弟之言,卻說向家表妹知道了,出來回覆道:『女子之嫁也,母命之。既是母親允了,為女兒的焉有揀擇之理?』遂留下這柄扇兒,又囑付一聲道:『前日之言,不要說起了。』如今年兄也須記著,後日閨房中言談之際,也只做個不知便了。」旭霞道:「自當領教。」 說罷暗想:「這扇子,若是成了親,自有活現的嬌娃親近了,要這樣鏡花水月何用?縱使他留在那邊,少不得仍歸我的。」乃道:「扇子原是令表妹故物,既留下,也不必說了。請問令姑娘尊意,要怎樣行禮呢?」 彥霄將姑娘所囑之言,述與旭霞聽了。旭霞心上十分歡喜,道:「既蒙令姑娘見愛,又承年兄玉成,待弟與家母舅商量定了,即日擇吉行聘。」彥霄道:「既如此,且暫別,另日恭候回音。」說罷,喚家人在扶手裡取這庚帖出來,付與旭霞收過,遂起身出門,上轎而去。 旭霞急忙忙的奔進去,說向母舅、舅母知了。正在那裡商議,恰好卿雲回來,述與聽過。那時三人計較定了,即差人去選了個行聘吉期,通知過彥霄,教他差個家人,一同送到崑山。然後整頓備禮,件件停當。 到這一日,請了冰人,畫船鼓吹,傘夫皂隸,鬧轟轟的送禮。在崑山宿過一夜,明日回吉轉來,比之去時,更覺熱鬧一倍。這時,杜老夫婦二人,真個歡喜無任。至於這衛旭霞,虛空思慕了三載,今已行聘,道是美貌佳人,不一月間就有得到手了,竟自樂極無量;乃與卿雲迎接彥霄,謝了一回,拱入園亭,開筵款待。外廳宴勞家人各役。准准鬧了一日而散。正是: 漂流三載得重回,復遇心交撮合媒。 締卻好姻消怨曠,一朝喜氣解愁眉。 那吉彥霄已謝宴歸家,這起回盤家人各役,也都領了犒賞,叩頭而去。不知這老夫人擇於何月何日,來迎旭霞去成親,且聽下回分解。 此是衛生丹成九轉時矣,又被杜、吉兩君一班鬼話,令人氣殺!然天下好事,決不易就,不氣殺,不樂殺也。
第二十一回 求凰遂奉命榮登任
華堂開選,冰人傳語,才子佳人進步。瓊筵綺席喜相逢,更勝卻登科無數。紅顏似畫,歡情如酒,鳳管鸞笙相助。兩情正洽赴瓜期,去永享皇家祿柞。 右調寄《鵲橋仙》 卻說那素瓊小姐,虧這旭霞的仙丹來醫好,這段快暢念頭,已是不消說得;更遇吉彥霄於中撮合,得與才子締了秦晉。三年向慕之私,一旦遂其志願,竟丟開了愁緒,不去胡思亂想。正在那裡心中暗襯,要打點繡個鳳枕鴛衾,恰好春桃在外,欣欣然的進來道:「小姐,老夫人方才教人去擇了成親吉日,明日要差人送去。聞說止隔得數日矣。小姐該做些要緊針線了呢。」素瓊道:「我也如此思想。你替我繡了兩副枕頭,待我自繡被心罷。」春桃聽了吩咐,去取出?來,上了繃子,復將絨線配勻了顏色,與素瓊對坐窗前,雙雙刺繡。 正繡得熱鬧之際,素瓊乃對春桃道:「我自從三年前同你繡了鄰家這幅做親生活,因這日那花嘴來,心上有些不快,丟了手,直至今日,覺得手中生荊棘來。」春桃道:「這幅生活,小姐患病之後,他家來催得慌,是我做完拿去的。」素瓊道:「原來如此。」春桃道:「我細想,小姐倒虧這一場病,今日原得與風流才子作配,力也不吃,做個現成夫人。不然,竟被那包說天哄去,做了膏粱俗子之婦,如今這衛老爺回來訪著了,難道不要氣死?我這裡聞得他榮貴還鄉,尚屬未娶,不要說小姐難存濟,就是小婢也要悔恨一番。」素瓊道:「倘我不生病,有人家說成了,我自然立志堅牢。原拚卻一死的,怎肯胡亂去錯配小雞!」 兩人正在挑繡忙迫、言談親切之際,只見碧霞走將進來道:「老夫人叫春桃姐出去,問些什麼置貨物件,明日絕早要往蘇州去的。」春桃收拾了針線,忙忙的走到外廂,老夫人喚進書房去,一個說,一個寫,足足裡寫了半日,才得完了。 春桃進房去,恰值抵暮了。素瓊問春桃一番,見得房中漸漸暗起來了,喚春桃出去點火進來,挑起銀□,坐於椅上,思想那仙丹包上四句詩兒,遂一句句如彥霄解說,都會意出來,乃贊歎道:「原來我與那衛生的姻緣,是早已定在他掌握中的了。」春桃聽了素瓊之言,問道:「小姐何以知之?」素瓊乃將這四句詩來,細細解說與春桃聽了。春桃遂恍然大悟道:「如此說起來,他的漂流三載,小姐的患病千日,俱是天意羈遲這樣一個大數在裡邊!」坐至更餘,春桃服事上牀去睡了。正是: 芳心暗數佳期近,怎得莊周蝶夢成。 到得明日起來,那老夫人將這吉期、置貨帳,都交付與兩個能事的老僕收了,下船而去。到了蘇州,那老僕先將吉日送至吉彥霄家去了,即到閶門置了雜貨,買就綾絹,歸來交付與老夫人。檢點明白,隨喚家人叫齊五色匠作,來家分派停當,鬧轟轟的造作器皿、衣飾了。不題。 卻說那吉彥霄領了姑娘之命,將這送來的吉期喚個家人拿了,一徑到卿雲家來。恰好旭霞回山去了,遞與卿云。卿雲接來一看,乃道:「吉日這樣近了,也要支值些事體。家表弟又不在此,怎處呢?」彥霄道:「吾兄可作速差一尊價,去請他到來才好。」卿雲道:「來朝當發舟,去接他至舍。」吃過茶,彥霄別去。 到得明早,喚家人引舟而去。宿過一夜,傍晚之間,旭霞喜色滿容的到來。那時,一家至戚相敘,商量整頓了幾日。凡一應做新郎所用之具,俱是為母舅者主張,十色完備了。 至迎親之日,彥霄袖了這把畫扇到來,卿雲設宴款待。正觥籌交錯之際,彥霄於袖中取出這扇,敬與旭霞道:「前日題和執照奉還了,年兄自去負荊面請了罷。」旭霞接在手裡,乃道:「年兄前云令表妹已留下了,何得今日又在兄處呢?」彥霄道:「前者小弟這番說話,只因向日見了年兄芳姿遺照,道是情癡之極,故敢相謔耳。家姑娘處,仙丹靈驗之日就允的了,今日是乘龍之期,恐兄到家表妹前對語起來,所以完璧歸趙耳。」旭霞道:「這段姻親,承年兄曲為玉成,豈不感激厚恩?但何可相契似兄如此惡耍?這幾日,幾何急死了小弟!」彥霄道:「聞得令表兄亦先為構辭嚇過一番的了。」旭霞道:「原來你們兩個是一黨的。」 說罷,遂袖了扇子,乃道:「專怪兩位暗地取樂小弟,各要罰金谷酒數,奉答雅情。」卿雲道:「我便領命,竟飲三杯罷。彥霄兄替你玉成了姻事,也可將功蓋愆了。」旭霞道:「既是表兄說人情,吃了兩杯罷。」說畢,出席將巨觥篩來敬上。彥霄飲了,乃道:「小弟也要奉旭霞兄兩杯。」旭霞道:「有甚差處受罰?」彥霄道:「也專怪兄會做芳姿遺照,一定要飲的。」旭霞只得默受而飲了。又共呼盧擲色一回。 恰好迎親的到了,在外大吹大擂過三通,開了正門,隨行逐隊,擁上廳來。分班立定,請杜老封君出去,叩頭畢,然後排筵款勞,也自傳杯換盞一番。歇了,掌禮傳事。旭霞換了烏紗帽、虹員領,簪上兩朵金花,拜謝了杜家一門至戚。卿雲、彥霄也更了公服。那時,三個一齊上轎,出門而去。你道好不榮耀!正是: 人生世上誰雲樂,大登科後小登科。 不題。 卻說那老夫人自發迎到蘇州去了,在家支值得齊整非常,真個是:玳筵前,秀楚寶鼎;繡簾外,彩結雕簷。屏開金孔雀,褥隱繡芙蓉。那老人看了,也覺喜不自勝。 不一時,鼓樂喧天的到來,先是彥霄出轎,進去商量過,到外邊來,於轎中迎出卿雲作了揖,拱入後堂吃茶去了。廳上打點結親,樂人吹擂起來。掌禮的請齊兩位新人,赴單交拜過天地,復去請老夫人出來受拜過,又去請卿雲、彥霄來見了禮,遂送入洞房,去做花燭。掌禮的執壺敬酒上筵,唱一調《滿庭芳》,詞云: 紅粉佳人,青錢才幹,仙丹撮參商。屏開射選,中目遂成雙。合巹芳閨綺宴,獸爐將蘭麝為香。分明是、蓬萊閬苑,仙子降華堂。人生此際,鴛衾鳳枕,得遂鸞鳳。願螽斯蟄蟄,熊夢呈祥。官至封侯拜將,壽比滄海長江。從今始、夫榮妻貴,瓜瓞永綿長。 掌禮唱畢,又敬上雙杯美酒,伶人作起樂來,熱鬧一番撤宴。旭霞到廳上去謝了冰人,復揖過卿雲,然後坐席。宴飲更餘,陪卿云。彥霄兩個到花園裡去宿了,轉身進來。 侍女春桃引入香閨中去,服事卸了公服,換卻紫衣飄巾,與素瓊一雙雙如賓如友,坐於花燭之下。白面紅顏,輝煌映耀。兩人你看我,我看你,各自心中暗喜。春桃開口道:「衛老爺,可記得三年前在支硎山,與我家小姐作揖了麼?」旭霞道:「這是日日銘心的,怎肯忘卻?那日蒙老夫人見愛,得親近小姐尊顏。」 春桃道:「老夫人倒不許的,虧這了凡師父使我家小姐識荊老爺。我道人家男男女女祈場佛會,那裡不邂逅的?偏是我家小姐與老爺會了一次,今日竟成姻眷,豈不是絕世無雙的佳事麼?」旭霞道,「想來原是天緣制定的,不然,何以一見之後,心上就日日想念,再不肯忘情?又得太白星托夢,尋仙授此丹藥,目今將來救好病體。」春桃道:「正是呢。」 正說話間,只聽得譙樓上鼓已三通。春桃乃對旭霞道:「不該是小婢催迫老爺、小姐,更鼓三敲,是夜分時候了,請去睡罷,不要錯過了吉日良時。」旭霞此時心中正欲如此,聽了春桃這句話,倒像是他發放一般的,滿面笑容對春桃道:「我不曉得你原來是一個妙人,說出這樣方便話來。」 素瓊聽了旭霞稱贊春桃之言,不知不覺的失聲一笑。旭霞此時,見得素瓊解頤巧笑,喜色盈腮,連忙跪下去,把住了他下半截道:「求小姐上牀去睡罷。有甚積衷,另日各自傾倒可也。」素瓊害羞,乃將衣袖掩了杏臉,只是不做聲。又是春桃見得如此,乃道:「衛老爺要小姐去睡,放尊重些。若是這樣屈體,不但是失了老爺的威儀,更恐今晚做出了樣子,後來那裡跪得這許多?」 旭霞道:「春桃姐,聞得你是知書識字的,這個意兒也不曉得?」春桃道:「小婢那裡識字?不曉得老爺是什麼意思。」旭霞道:「這叫做男下於女的大禮。」春桃道:「老爺既是曉得這禮的,何不起來向我家小姐深深作個揖兒,包你就依。」旭霞聽了春桃,果然立起身來,叫一聲:「小姐,謹依尊侍女之命,真個奉揖了。」 說罷,整整衣冠,恭恭敬敬的作個揖下去。素瓊此時,忍不住櫻桃絳口又失聲一笑、也還了一個禮,又且彎了柳腰去扶旭霞。旭霞見纖玉手扶他,那時喜得魂不附體,捋衣袖去勾了素瓊的粉頸,雙雙步上牙牀,掛起銷金繡帳兒,卸下衣裳,忙入鴛衾裡去。此時兩人貼肌貼肉,交頸歡娛,何得還有閒功夫去說長話短?正是: 歡娛一刻千金價,只恐司晨雞亂啼。 到得明日起來,旭霞先自梳洗過,出去支值。卿雲,彥霄兩個下船回去了。復進房去,換了幾件簇簇新的佳麗衣服,打扮得飄飄拽拽,坐於妝台之側。一面將這把畫扇故意捻在手中揩磨,一面細看素瓊梳妝。春桃走來拭頭服侍,立於素瓊背後,見了乃道:「老爺什麼扇子,如此珍玩他?」旭霞道:「不瞞春桃姐說,覷他外材便是平常,若揭開看時,竟是一件至寶。我已得之三年矣,再使人摩弄不厭的。」春桃道:「莫非老爺在仙家得來的活寶?」旭霞道:「也不是仙家活寶,是人世間第一件活寶也。」 此時素瓊聽了,心中驚駭,暗想一回,忍不住開口交談了,低低的道:「可與我一看?」旭霞雙手敬與素瓊。素瓊接在手中揭開看時,忽然驚訝對春桃道:「這也奇怪得緊!那把畫扇,是我家三年前所失之物,曾與你在尼庵裡疑想了許多,豈知竟在他處!若依目下論來,這起課者,原有八九分應驗的。」春桃也來仔細一看,只做不曾見的模樣,道:「小姐向日是畫什麼在上的?莫非不是?」素瓊道:「自己的筆跡,難道不認得?」 春桃又來假意看看,乃道:「小姐這日畫了瞞我,我道為著恁般緣故。欲要吹毛求疵,恐犯小姐之怒,遂不敢問及。卻原來是預先畫就老爺。小姐的一幅行樂圖,故爾此時失了,小姐廢寢忘餐的思想。」旭霞乃接口道:「我有何德,往蒙見愛若此,費這樣芳心!」說罷,素瓊不免細細查問旭霞在何處得的來歷,旭霞亦自推求其畫扇、失扇情由。只見外面進來,請出去見禮祭祖。恰好此時素瓊的雲鬢已梳就了,遂各自換了公服,出去行過大禮。 進房來,復易了褻服。旭霞把這自始至終事跡,述與素瓊聽過,不免驚異一番。素瓊亦將愛慕才子這些暗衷愁腸,也自細細傾倒與旭霞聽了,亦自贊歎感激一番。素瓊乃去取出這詩箋來付與,旭霞接在手裡,對著他道:「小姐,不要輕覷了這句俚言來,竟是一片御溝紅葉。更於那個了凡家姐,亦不要得魚忘筌了他!與小姐乍會,此夜若沒有了凡灌醉小姐,在他臥榻上邊,我與小姐兩個,何由得預上陽台,雲雨這一番?」 素瓊道:「這是那裡說起?是夜老夫人問及你,了凡說道:『恐怕男女混雜,一來不便,二來懼奶奶見責,回他去了。』母親此時就憐惜過你一番的。況且我天性又是不飲酒的,家母道是在外食則同食,寢則同寢,時刻不離防閒拘管的,那裡被他灌醉?那裡臥在他榻上?且如此我是何等樣人了?這也真個可笑得緊!出家人這等造孽,所以叫他死去游地獄耳。」 旭霞聽了素瓊這番正言厲色,覺得驚駭了半晌。想著了三年前托夢後的想頭,會意了,即左支右吾了素瓊幾句。恰好老夫人進房來,大家坐定,也自敘過了些始未,出去了。以後那夫妻二人,琴調瑟協,如漆如膠的度日。 不道光陰易過,倏忽是旭霞憑限到任之期。接官的衙役到來,發了打掃牌告示去,遂留下兩個門子皂快隨身。擇了長行吉日,與老夫人計議定了,將家私細軟什物發扛下船,僉了宅子門首張掛的告示封條,遂把房屋傢伙交付與兩個老僕看管,遂同了老夫人一家眷屬,登舟發棹。 到了蘇州地面,泊船葑門外靈官廟前,打轎上岸,到母舅家去拜謝大恩。杜家不免開筵會親。過了宿,明日旭霞與素瓊商量道:「我與你兩人得諧伉儷,雖是由令表兄之力,論起那個了凡家姐,就是有這番得罪於小姐處,原其情,此夜不過為雲仙作撮合耳,諒亦本無大罪。我們發始之初,虧他師兄弟兩個引進的。為人在世,豈可因好事成了,遂忘情於起頭之人?今日到令表兄處去了,我道畢竟還該到庵去一遭,心上才得安穩。」素瓊道:「我也不記他過了,但你姊妹間,論起理來,也該酬謝他一番。」旭霞道:「小姐之言,不但是寬洪度量,抑且出言明達。既如此,到彥霄家去了,另喚一隻小船去罷。」 說畢,別了杜家一門至戚,遂到吉家去,亦宿過一夜。明日起來,叫鷓兒喚下一隻遊山華舫,帶著傘夫皂隸,一齊下船。不上半日,到了支硎山下,打轎上岸,依回曲折的過嶺而去。至山門前,有人進去報告。雲仙曉得了,出來迎接進去,歡歡喜喜的相見過。了凡在關內,也自問訊了。大家敘過闊情。旭霞與了凡仍舊姊妹相稱。了凡不免問起成親之事,稱暢一番,遂叫雲仙收拾點心留了。臨別時,旭霞感兩尼昔日之恩,喚門子拿扶手來,取出紋銀二十兩,付與了凡,助他修行薪水之資,然後別過,出山下船。因晚了,在店橋過了一宿。 明日行至葑門,過到坐船裡去,大吹大擂的解維發棹而行,望嘉興府到任去了。正是: 人間莫大是姻緣,共枕同衾豈偶然。 縱使兩情河海隔,一朝撮合永團圓。 不知他為司李之職作何狀貌出來,且聽下回分解。 春桃姐極似今日門客。然今日門客有其醜態,無其慧心。人生得意事,盡在此回。
第二十二回 解組去辟谷超仙界
姻就名成,凌雲志展。仙家戒諭言非淺。異花瓊漿色鮮鮮,杯傾換骨分枝瘈。解組歸山,世情須遠。雙雙辟谷辭塵絆。一朝會舊續仙緣,鸞驂鶴駕起蓬苑。 右調寄《踏莎行》 卻說那張紫陽在仙境,曉得衛旭霞完婚到任去了,恐他耽於酒色財氣,誤陷塵網,難超仙界,與鳳瑞珠續敘仙緣。一日去拉了瑞珠女仙,於石室中取一瓶換骨瓊漿,三枝洗塵不死花,置在花籃之中。紫陽駕了白鶴,瑞珠乘了彩鸞,一齊騰空,渡海飛行。 不上半日,到了嘉興府城中,乃留鸞、鶴於雲端,冉冉從空而降,來至府前,變就兩個道人,提著籃兒,立於街坊張望。適旭霞公出回廳來,在路上見了,紫陽、瑞珠走上去,一把拖住了轎兒,口裡連連告道:「求老爺佈施。」這起各役把他亂踢亂打。 旭霞道是奇異,連忙喝住手下,帶他回廳去。坐堂問他道:「道者,你為何不向市廛中去抄化,反來攔截我道子呢?」紫陽道。「貧道不滿老爺說,我們兩個雖是化緣,原有一番氣概,非沿街抄化者流,故誓有『五不化』:市井貪夫不化,慳吝守財虜不化,貪官污吏不化,無宿根善念者不化,不知進退、迷戀聲色者不化。今聞老爺為官清正廉潔,處心積慮,自是不凡,貧道所以特來募化。願老爺大破慳囊,化與我紋銀壹萬兩。貧道把去替老爺做些閒雲野鶴、世外非凡之事。後來老爺回頭登岸,可以安享不盡。」 旭霞聽他一番議論,隨想他不是等閒化緣的,心裡另自待他,口裡乃詭言試之;且見那個女道不言不語,不知何故,乃問道:「你兩個是夫婦、是兄妹呢?有許多年紀了?」道者道:「非夫妻,非兄妹,不過同伴抄化遨遊的。若說年紀,寒寒暑暑,不知過了許多,記不起了。」 旭霞道:「倒也可笑。為人在世,雖是遊方曠蕩,不要終老,難道連自己的年紀也忘卻了?明是奸邪之徒,我這也不計較了。但你兩個一男一女,既非夫妻、兄妹,如此同行同宿,圂帳過日,怎得潔然不污,如柳下惠、魯男子乎?」 紫陽道:「老爺差了。可曉得『淫污』兩字麼?凡夫俗子,迷戀女色,沉淪欲海,終身莫悟,乃不得超世者。若養真修煉之摯,愛惜精神,念念保固,不肯絲毫滲泄,所以內濾外凝,雖豔冶當前,如過眼空花,漠然無所動於中。所以貧道男女同行同宿,爾為爾,我為我,絕不起妄想,以喪天真。」 旭霞聽了,不覺毛骨皆竦,恍然大悟,拍案贊道:「道人,善哉!汝言俱是透徹妙道之論。我今捐俸與你百兩,去作修煉之資何如?」紫陽道:「既蒙慨許,貧道們今日去了,明日來領。」旭霞道:「你們兩個來得久了,到我私衙裡去齋你一齋。」 紫陽、瑞珠攜了花籃,隨著旭霞退堂進去。兩人站於廊下。旭霞到裡面去,與素瓊、老夫人兩個述此奇異。說猶未了,承值的進來報導:「老爺,方才要齋那道人,如今那兩個影兒也沒了,只存得一隻花籃在外邊。」 旭霞倒吃一驚,連忙出去看時,真個俱不在了。啟他的籃來細看,只見一個瓷瓶兒,緊緊封好的;又有鮮灼灼的三枝異花在內。隨即拿到裡面去,與老夫人、素瓊三人細玩。捻在手中,覺得芳香襲人,光彩耀日,各各稱奇。旭霞乃差衙役去滿城追尋,杳然無從蹤跡,來回覆了。旭霞對夫人說道:「我始焉原道他兩個奇異,故帶回盤詰他。他談吐津津,頗多仙氣。如今且把這花與瓶原替他放在籃裡藏好了,看他如何。以後眼巴巴看他來那裡有個影響?」 旭霞見他不來,把那籃中的花拿出來看看,並不見枯槁,鮮豔如舊在那邊。大家驚贊一番,仍藏好了。不知不覺將過半載了。 偶值中秋,月色溶溶,旭霞同老夫人、素瓊在衙署賞月。清光照席,佳人才子,觴酌羅前,暢敘幽情。旭霞乃忽想看籃中花朵與瓶,叫春桃進去取來。把金瓶插了三枝花在內,供於桌上,稱美一回。又將瓶開了,覺得芳馨撲鼻,乃對夫人道:「異品不可輕褻。」叫春桃取一對玉杯來,慢慢傾了一滿杯。仔細一看,色似桃花,光如寶璨,想道:「莫非仙液瓊漿?不知恁般滋味。」將來呷了一口,覺滿嘴甘香,沁入肺腑,乃贊歎道:「我在雲林夫人宮中吃的美酒,此味便覺相像。」索性一飲而盡。復傾一杯,遞與素瓊。 素瓊接在手裡道:「我酒是不飲的,但是老爺如此贊美,想必異味。」乃慢慢上口,也一飲而盡,覺得遍口生津,滿腔滋潤,乃驚訝一回。旭霞把瓶盡情傾在杯中,恰好還有不淺不滿一杯,將來敬與老夫人道:「岳母在上,不是為婿的無禮,不先敬大人。此正湯藥子先嘗之禮也。」老夫人道:「既是瓊漿玉液,我是年邁之人,用不著了。原是你們兩個飲了罷。」 春桃聽見老夫人不欲飲,乃道:「太奶奶倘小心行,春桃飲了罷。」老夫人隨即授與春桃。春桃雙手接來,傾入櫻桃小口,嚥下清俊香喉,乃道:「抄化道人身邊有這樣嘉美之物,真非人間可得者。」素瓊道:「癡丫頭,那一個說他是抄化的?自然是神仙耳。」春桃道:「若是神仙,少不得還要來應驗。」素瓊道:「想必是老爺做官清廉,天遣他來賜這兩件異物,或這就是應驗亦未可知。」旭霞道:「下官沒有人褒獎。夫人之言,倒講得妙。」 說罷,復飲酒幾杯,清談一回,覺得露寒月轉,更鼓連催,是將夜分時候。老夫人道:「如此皓月良宵,本該深賞,但賢婿官政繁冗,明早要理事的,不宜久坐勞費精神。你們夫婦再飲幾杯,收拾進去歇息了罷。」旭霞道:「岳母真老成之言。」遂立起身來,將這三枝花與素瓊、春桃各自捻了一枝。老夫人在前,引了旭霞夫妻、侍婢三人,月下輕移環佩,攜手同行。恰似神仙歸洞天的進去了。正是: 賞心樂事良宵宴,飲卻瓊漿骨自更。 旭霞睡了一夜,明日起來理了些政事,以後遂悠悠忽忽過去。 光陰迅速,倏焉是滿任之期了。旭霞夫妻三人因飲了瓊漿之後,覺得日漸一日,身體輕鬆,欲情俱淡,飲食少進,似有辟谷之狀。心裡各欲恬養求安,不喜膏粱紈綺。 恰好瓜期已足,聞得撫台上疏薦過廉能,旭霞恐復任報來,忙赴撫台處去,將冠帶印綬交割辭官。撫台著實留他,旭霞抵死辭脫了。歸所即忙吩咐,一面發扛下船,一面自去拜別了堂尊廳僚,清清靜靜的起身。豈知驚動了合府子民,攜老摯幼,執香而來,脫靴拜送。直至旭霞下了船,留連遠望,目送而散。正是: 若遇官清正,百姓俱安樂。 一朝辭任去,口碑載城郭。 那起人民都是泣涕回去了。不題。 卻說那衛旭霞回到蘇州,泊船上岸,至母舅家去,留下兩日。吉家也去過一次。乃發舟到崑山岳母家去住下,終日與素瓊、春桃三人在深閨中焚香烹茗,吟詩作賦。 倏焉又過了幾年,豈料這三人因吃過寒冷瓊漿,竟爾都不能生育。旭霞夫妻已似有了仙氣,這些榮華富貴、子女玉帛,竟置之度外。惟那老夫人時年六十有七,見得婿、女兩個成婚長久,不生男育女;更兼見他終日脫然駘蕩,終不以乏嗣為憂,老夫人心上未免終日鬱鬱不樂。豈知一日積悶成病,陡然發起來,延醫服藥,竟不肯痊,遂淹淹溜溜三四個月,竟自死了。 旭霞乃好好成殮了,治喪塋葬之後,因自己妻妾三人,心懷僻靜,思慕山居,忽起遷歸長圻之念。但若岳母一抷之土未乾,不忍竟自拋撇而去,更兼岳父沒有本支姪輩承受家業、香煙,與素瓊商量,竟自備起酒來,請了許多親族,擇一遠房賢能姪兒,接了岳父母香火,把他家產一一開明,交付與他了。然後摯其妻妾以歸蘇郡,於母舅處住下,同了素瓊出去遊山玩景。 正值小春中旬,是老夫人的生忌,素瓊要到支硎尼庵去追薦他。旭霞聽了,遂欣然備了齋供之儀,一徑到尼庵裡去。你道好不湊巧!恰遇著了凡生化昇天之日。旭霞這一起走進門去,見得熱鬧非常,乃問道:「作何道場,如此齊整?」眾道友道:「了凡師父今日昇天,我們在這裡奉送。」 旭霞夫婦三人聽了此言,倒著一驚,遂又問道:「雲仙師父在那裡?」眾道友道,「他已先亡化過四年矣。」旭霞復想起昔年之情,不覺撲簌簌的淚如雨下,哭了一場,遂教道友引至了凡坐化之所去看。只見他身披袈裟,手執如意,露頂盤膝,趺坐在氈單上。 旭霞夫婦三人見了,各自流淚,拜了兩拜起來,贊歎一回。索性不說起追薦之事,竟將這些帶來的齋供擺設於了凡、雲仙兩處,又加祭拜慟哭一番,送他入龕□過。然後歸到母舅處,拜別了,起身歸山去住下,鎮日山蔬野菜的度日。 不覺又是三、四年之後,竟自辟谷了。杜、吉兩家聞之,道是奇怪,俱來看過幾次。 一日,旭霞絕早起來,吩咐鷓兒到蘇州接杜、吉兩家親戚,教他作速到來。鷓兒連忙到郡去說了。杜、吉兩家以為駭異,男男女女俱至山來。旭霞夫婦相見過,遂把家私什物,付與鷓兒夫妻兩個收管過,乃對眾親道:「我們至戚相敘世間,原為美事,豈料今日一旦要拋撇公等,在明午牌時候,當升虛而別了。」眾親戚聽了,不覺傷心一回,依依相敘的過了宿。 明日起來,旭霞原教小鷓兒收拾早膳與眾親吃了,遂喚他燒起香湯來。妻妾三人俱浴淨了身,上來拜別眾親。眾親同了鷓兒,一齊慟哭起來。旭霞道:「這非死別割愛,不消悲慟得。夫凡人生紅塵中,情慾相牽。到生老病死了,原是一場虛氣。我今日到這個地位,只樂得無掛無礙,飄然而去。到了仙境,自有一種清虛快樂之福,何勞尊長輩傷心?」說罷,遂同素瓊、春桃一齊下拜眾親畢,又望空拜別了亡化先靈。只見一鶴一鸞,飛舞庭中,繞屋祥雲擁護。 旭霞量道午牌時候了,遂將三枝花各自執過一枝;又把這瓶兒盛於籃中,命春桃提了在庭中俟候。只見張紫陽同了鳳瑞珠,又有無數仙童仙女,在雲端作樂。旭霞妻妾三人見了,跪於庭中,羅拜為接。 先是紫陽、瑞珠兩個冉冉而下,旭霞起身,拱入廳裡。那張紫陽道:「我今日特奉雲林娘娘之命,引四時苑主鳳瑞珠仙姑到來,與文士續配了仙緣,召駕臨宮,去司萬卉之文章,掌一宮之仙眷。更宣天孫素瓊、記室春桃,一齊發駕。鶴馭鸞驂,俱已整備在庭,毋得欠延凡界,動人窺看,以泄仙機。」 說罷,紫陽呼喚仙童仙女下雲端來,至廳前,並奏雲璈,聲音徹天。那時,張紫陽請鳳瑞珠來與旭霞交拜。待過了夫婦之禮,然後與素瓊亦行了仙班姊妹儀文畢,各自乘鸞駕鶴,騰入祥雲,飄然而去了。 卻說那些親戚,見他們白日昇天,不免望空遙拜而送,直至不見了起來。男男女女,倒嚇得如癡如夢一般。更驚動了長圻一村老少,挨挨擠擠的來看,再沒一個不贊美稱異。到得明早,杜、吉兩家親戚,覺得至戚生離,不免自心中怏怏,俱是依依不忍,下船而歸。抵家時,旭霞平日這起相知朋友、兩家因親及親的眷屬聞知,都來詢問贊歎一番而去。 以後,杜卿雲雖不及做表弟的白日成仙,他的雙親叨受皇恩,誥封壽終。營葬之時,空中飛下雙白鶴來弔,似有悲切之狀。揣度起來,自然是旭霞夫婦變化到來,謝昔日之恩。那卿雲官職,做到兵部侍郎而止。所生二子,亦是發科發甲,書香不絕,也可稱人世仙境了。 那個吉彥霄,出身就是年少詞林,聖上嘉其才藻,特賜大學士以終其身。封妻蔭子,極其華麗。後嗣綿綿,爵祿靡窮。 至於那個山鷓兒,雖雲奴僕下賤,家主漂流之後,曾為陰告陽申一番,滿腔義氣,故爾旭霞升仙之日,感念其情,遂將家產交付與他。以後乃自成一家,生男育女,勤儉經營,做了一個山村富室。竟接受了旭霞祖宗的香火,逢時遇節,替他祭祀,以故里中之人俱欽敬他,咸稱為忠厚長者,壽至八十而終。豈非千古流傳之佳話哉! 鳳瑞珠與衛旭霞世緣已絕,復結仙緣。「緣」之一字,甚是情種,無論仙凡,但不容即斷也。但不知素瓊有妒無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