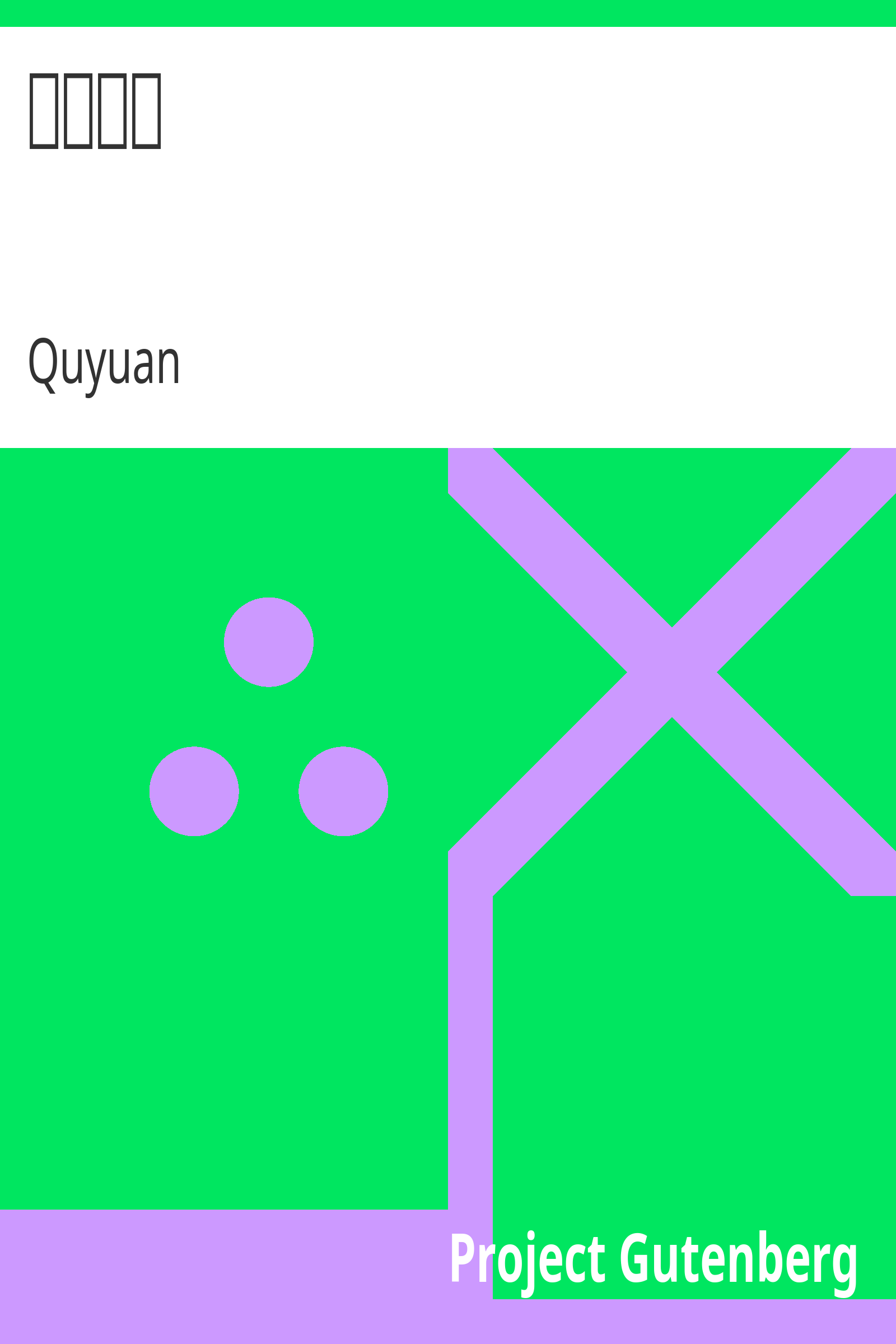負曝閒談
Play Sample
先問老頭子,老頭子道:「我好好的邊兒上走,他把我一碰,碰倒在地,跌得我週 身生疼,我正要找他呢。」又問小桐,小桐提著他那條賣估衣的嗓子,說道:「他倒說 乾淨話兒!我提著雀籠,也在邊兒上走,這老王八一晃一晃的碰到我身上來,把我雀籠 碰在地下,成了兩半個。這雀籠呢,原不打緊,倒是我那個百靈是個無價之寶,什麼都 會叫,貓叫、狗叫、馬叫、驢叫,還有笙簫鼓笛,件件齊全。這兩天又學會了外國山歌 。
你們想想,可愛不可愛?這一下可跑了,不是去了我的命嗎?」
他說得出便做得出,登時號啕大哭起來。那老頭子急得目瞪口呆,計無所出。
小桐一頭哭,一頭還嚷道:「誰把他放走了,咱們白刀子進,紅刀子出!」等他哭 完了,又是劈胸一把,說:「咱們上刑部衙門去!」那老頭子嚇得身體如篩糠一般,便 央求眾人道:
「眾位朋友,給我撕扌羅撕扌羅,我定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!」眾人又勸小桐道: 「你剛說要他賠,他現在肯賠了。你到底要多少呢?」小桐把指頭一伸道:「一百兩。 」老頭子道:「豈有此理!一個百靈值到這個價,你簡直是訛我了!」小桐啐了他一臉 唾味道:「我把你這王八羔子!你就是賠了我一百兩,我還不願意呢。走,咱們上刑部 衙門!」老頭子央求眾人道:
「諸位大哥,你們公公道道,替我酌量個價錢吧。」眾人道:「一百兩呢太多,八 十兩是不能少的了。」老頭子初還不肯,眾人做好做歹的,逼他出了六十兩銀子,說明 白跟他回寓去拿,這裡眾人才一哄而散。
小桐拿到了六十兩銀子,回到家中,剛才在外面飛掉的那只百靈,好好的在那裡啄 小米了吃了。原來他是養家的,常常借此訛人的。正是:
畫虎畫皮難畫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四回 擺架子空添一夜忙 鬧標勁浪擲萬金產
上回書說小不要臉桐訛人的那些故事,這回再說他父親老不要臉桐。原來老不要臉 桐,起初家道極貧,住在爛面衚衕。
家裡窮的淌尿,他還要滿口大話,架弄他的身分。他住的宅子,倒是他祖上留下來 的,到他手裡,又沒有錢去修理,弄得破敗零落,很像一座古窯。他隔壁住的乃是一位 戶部郎中,名叫文璧,是蒙古鑲紅旗人氏,和老不要臉桐還沾親帶故。文璧的書室,緊 貼著老不要臉桐的上房。
有一年秋天,文璧喝醉了酒,回家一覺瞢騰大睡。及至醒了,已經是酉牌時分了。 想要再睡卻又睡不著,便一個人點了個燈,到書室裡來寫信。只聽見隔壁老不要臉桐叫 著丫頭道:
「來啊,拿我的帳子掛起來。」丫頭道:「老爺什麼帳子?」他道:「是白的。」 丫頭道:「連黑的都沒有,別說是白的了!
」他說:「是長的。」丫頭道:「連短的都沒有,別說是長的了!」他道:「是把 繩子繫住的。」丫頭道:「連不把繩子繫住的都沒有,別說是把繩子繫住的了!」過了 一會,丫頭道:
「哦,哦,哦,我知道了!」帳子的事情完了,老不要臉桐又道:「來啊,把我的 枕頭墊起來。」丫頭道:「什麼枕頭?」
他道:「是高的。」丫頭道:「連矮的都沒有,別說是高的了!」他說:「是方的 。」丫頭道:「連圓的都沒有,別說是方的了!」他說:「是硬的。」丫頭道:「連軟 的都沒有,別說是硬的了!」又過了一會,丫頭道:「哦,哦,哦,我知道了!」
枕頭的事情完了,老不要臉桐又道:「來啊,把我的被窩鋪起來。」丫頭說:「什
麼被窩?」他道:「是寬的。」丫頭道:
「連窄的都沒有,別說是寬的了!」他說:「是厚的。」丫頭說:「連薄的都沒有
,別說是厚的了!」他說:「是直的。」
丫頭道:「連橫的都沒有,別說是直了的!」又過了一會,丫頭道:「哦,哦,哦 ,我知道了!」北方節令較早,這年雖是七月,天氣已經很涼了。只聽老不要臉桐道: 「今兒晚上,有點涼颼颼的,我把皮袍跟著靴子都穿上吧,省得明兒鬧咳嗽。」
文璧也不在其意,把朋友來的信,復了一封,又是一封。
一直寫到天亮,有些倦了,伏在桌上打盹。猛然間聽見隔壁老不要臉桐屋子裡「嘩 唧」一聲,文璧登時驚醒。只聽丫頭嚷道:
「老爺,你的靴子打爛了!」文璧十分詫異,心裡想:「靴子怎麼會打得爛?就是 打得爛,為什麼會這樣響?」正在疑疑惑惑。聽見老不要臉桐打了幾個呵欠,說:「天 不早了,該起來了。」說著,又聽見他叫那丫頭道:「金鈴兒,金鈴兒,你也起來吧! 太太昨兒晚上上王府去吃酒看戲,沒有回來。你該早早的梳好了頭,洗好了臉,套車去 接才是。」丫頭應了一聲。
旋即聽見老不要臉桐穿衣裳的聲音,打火的聲音,吹著了煤紙抽潮煙的聲音。又聽 得叫道:「來啊!你把枕頭放到台階底下去!把被窩安到門框兒上邊去!」丫頭答應了 ,忙亂了一會。老不要臉桐又道:「你再瞧瞧,帳子還有沒有?皮袍還有沒有?」丫頭 道:「帳子燒完了。皮袍喝完了。靴子打爛了。」
文璧更是不懂,進去告訴了他太太。他太太聽了,也稀罕得很,悄悄打發一個老媽 子順便去問那丫頭。等到文璧衙門裡下來,太太迎著告訴他道:「剛才老媽子過去,把 老不要臉桐的事情一齊打聽明白了。你知道他帳子是什麼?原來是蚊煙!」
文璧道:「還有枕頭、被窩呢?」太太道:「枕頭是台階底下撿得來的磚頭,被窩 是門框兒上脫下來的門。」文璧道:「靴子怎麼會打爛?皮袍怎麼會喝光呢?」太太道 :「靴子是酒罈子,皮袍是酒。」文璧這才恍然大悟。繼而一想,拊掌大笑,不知不覺 把眼淚都笑將出來。
過了一陣,文璧看他漸漸的光鮮起來了。一打聽,才知道投著了一個主兒,所以吃 喝穿著都不愁了。你道他的主兒是誰?
原來是木魯額木中堂的大少爺。木中堂在日,做過文淵閣大學士,執掌軍機。他的 大少爺名字叫做春和,號蔚然,北京城裡算是數一數二的闊少。什麼都不用說,單說是 鼻壺壺一項,也值個十多萬金。京城裡人用鼻煙壺有個口號,叫做春玉、夏晶、秋料、 冬珀。玉字所包者廣,然而綠的也不過是翡翠,白的也不過是羊脂。晶有水晶、有墨晶 、有茶晶、還有發晶。料的那就難說了,有要是真的,極便宜也要五六十金。還有套料 的,套五色的,套四色的,套三色的,套兩色的,紅的叫做西瓜水,又叫做山楂糕,黃 的有南瓜地,白的有藕粉地,其餘青綠雜色,也說不盡這許多。春大少爺春和,他除掉 這些之外,還有磁鼻煙壺。磁鼻煙壺以出自古月軒為最,扁扁的一個,上面花紋極細, 有各種蟲豸的,有各種翎毛的,有各種花卉的,有各種果品的。春大少爺他有不同樣的 磁鼻煙壺三百六十個,一天換一個,人家瞧著,無不納罕。
京城裡有個槓房頭,也講究此道。他單有一個料鼻煙壺,上面刻著兩個老頭子,又 刻著兩個小孩子,一個編了條辮子,一個囱門口留著一搭胎發。據說這個壺的名字,叫 做「七十九,八十三,歪毛兒,淘氣兒。」是頂舊的舊貨,現在再要找也找不出來了。 有天,這槓頭在茶館裡誇說:「咱這壺,無論什麼人,他都不配有!你們別瞧木府那麼 闊,他們的壺那麼多,要找得出一個跟這同樣的,我把這個砸碎它!」眾人聽了,默無 一語。便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春大少爺聽。
春大少爺聽了,這一氣非同小可。心中暗想:「這小子如此可惡,必得蓋他一下子 !」叫人把裝煙壺的匣子搬下來,自己細細的檢著,檢了一天,果然沒有這件東西,心 裡納悶道:
「這回輸給這小子了!」誰想他兄弟成二爺成貴,看見他哥哥面上有點不自在,便 問他哥哥為了什麼事。春大少爺如此長短,告訴了他一遍。成二爺道:「七十九,八十 三,歪毛兒,淘氣兒,這個壺不能沒有!」沉吟了一會,又說道:「咱們老爺子有這麼 一個,不知道是賞給了誰了。」正說著,他府裡的老家人王富便上前回道:「老中堂有 這麼一個,在世的時候賞給了奴才了。」子春大少爺一聽,大喜道:「這話真嗎?」王 富道:
「奴才不敢撒謊。」春大少爺道:「現在還在不在呢?」王富道:「奴才為著是老 中堂賞的,不敢拿出來用,現在還好好的藏在家裡呢。」春大少爺一疊連聲道:「你快 去拿來!你快去拿來!」不多時,只見王富捧了個紫檀木匣子,打開來把棉絮扯掉,露 出壺來。春大少爺把它放在掌心,兩邊細看,和槓頭的一模一樣,而且槓頭那壺,口上 缺了一粒米這麼大,木中堂賞給王富的這壺,一些破綻沒有。春大少爺大樂,掖在腰裡 四喜袋裡,匆匆忙忙吃完了飯,騎著牲口便去找那槓頭。
那槓頭可巧不在家中,出門去了。春大少爺一團高興,登時打滅。回來之後,家人 們去打聽,知道這槓頭天天在前門外一爿清風居茶館裡喝茶的。第二天一早,春大少爺 便趕了去。
槓頭恰恰在那裡聞煙呢,春大少爺便朝他說道:「你是說過的,誰能夠找出一個跟 你合樣的壺來,你就把你那壺砸碎。這話可是有的麼?」槓頭抬頭一看,見是春大少爺 ,連忙站起,說:
「大爺別聽他們混說!。」有個旗人德王,在旁岔嘴道:「那天你自己說的,我還 在旁邊聽見的呢。你今兒想賴可不成!」
槓頭兩臉漲紅,一聲也不言語了。春大少爺把壺掏出來給他看道:「你瞧瞧,夠得 上你那個,還夠不上你那個?」大伙兒聽見了,便圍上來了。春大少爺拿槓頭的那個壺 ,又拿自己帶來的那個壺,對著大伙兒道:「你們都是行家,瞧瞧誰的好,誰的不好? 」大伙兒都認得春大少他,哪有不奉承春大少爺的。
春大少爺舉著槓頭那壺說:「是你自己砸,還是我替你砸?」
槓頭見事不妙,便嘻皮笑臉的把壺搶在手中,一溜煙逃走了。
春大少爺這回得意非同小可,回到家中坐下,便叫人把田地房產契券的箱子搬來, 掏出鑰匙把箱子開了,翻出一搭市房的契紙來。隨手檢了一張,原來是花兒市的一所房 子,每年可得租價一千多銀子,留在外面。叫把箱子搬了進去,便對王富道:「拿這所 房子,跟你換這個壺吧!」王富歡喜之狀,也就難以言語形容了。春大少爺手筆如此之 闊,這回老不要臉桐黏上了他,豈不要發財麼?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
話說老不要臉桐自認識春大少爺之後,車馬衣服都漸漸的架弄起來。春大少爺本是 個糊塗蟲,只曉得鬧標鬧闊,於銀錢上看得稀鬆。老不要臉桐又是老奸巨猾,始而買東 西上賺點扣頭。有些家人們妒忌他,他倚著和春大少爺要好,任憑他們如何妒忌,只是 沒奈他何。
光陰荏苒,已是隆冬時候了。有天,春大少爺在估衣鋪裡瞧見一件索庫倫的貂馬褂 。原來這索庫倫是老貂皮,毛深而緊,與那些秋貂冬貂大不相同。春大少爺用五百銀子 買了回來,十分歡喜。十二月初一,是他母舅華尚書壽誕,他在華尚書宅子裡充當戲提 調。這天定的是玉成班,一早掌班的戲箱發來了。
春大少爺穿著白狐開氣袍,套著海龍馬褂,腰裡掛著鮮明活計,都是長圓壽字的, 嚷著叫家人單拾掇一間屋子。家人們請示:
「單拾掇一間屋子乾嗎?」他又嚷道:「單拾掇一間屋子,讓叫天兒抽煙呀。」家 人們唯唯的去了。少時,拜壽的絡繹而來,都是些什麼尚書、侍郎之類。春大少爺張羅 了這個,又去張羅那個,早忙得他氣喘如牛。等到開了席,端上面,他匆匆忙忙的吃了 一碗,擦過臉,鑽到戲房裡去了。
那時台上已唱過兩三出吉祥戲了,他四邊一望,只有小朵兒一個在那裡扮妝呢。他 便走過來,替他理簪環,調脂粉,亂了一陣子。外邊一疊連聲說;「大人請春大爺!」 春大少爺跑到了裡邊,華尚書正在那裡聞鼻煙呢。他說:「舅舅有什麼話吩咐外甥?」 華尚書道:「沒有別的,前回軍機上陸大人說過,他喜歡聽叫天兒的戲。今天他有事, 光景下半天才來,你好好的叫叫天兒伺候著,別走開,回來找不到。」春大少爺答應了 幾聲「是。」退下去便嚷著叫家人們去催譚老闆。家人們說:
「催過了,譚老闆還睡在被窩裡呢!」春大少爺打身上掏出表來一看,道:「現在 已經十二點鍾,他怎麼還不起來?真混帳!」家人們說:「他傢伙計提過,就是上裡頭 當差使,也得兩點鍾才去呢!」春大少爺無言可答。一會兒,小朵上場唱過了《花田錯 》,便是孫怡雲的《宇宙鋒》。孫怡雲《宇宙鋒》完了,是李吉瑞的《長板坂坡》。這 時已經兩點多鍾了,陸大軍機也來了,春大少爺本來認識,上去見過了。陸大軍機只說 得一句:
「今兒你當提調辛苦了!」便扭轉頭和華尚書說別的去了。春大少爺在上頭沒有意 思,便又溜進戲房裡。看看戲單:
李吉瑞的《長坂坡》下來,是金秀山德王君如的《飛虎山》;《飛虎山》下來,是 餘莊兒的《馬上緣》;餘莊兒的《馬上緣》下來,就是叫天兒的《討魚稅》了。春大少 爺跺腳道:「怎麼還不來!怎麼還不來!」道言末了,家人趕進來說:「譚老闆來了! 」春大少爺大喜,趕著跑出來,只見叫天兒穿著猞猁猻袍子,翎眼貂馬褂,頭上戴著皮 困秋兒,皮困秋兒上一塊碧霞璽,鮮妍奪目;後頭跟著伙計,拎著煙槍袋,挾著衣包, 另外還有行頭。春大少爺便說:「秋峰,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呢?」
叫天兒慢條斯理的道:「起遲了,累您等了。」春大少爺便讓他到剛才拾掇的那間 屋裡去坐。
叫天兒進了這屋子,伙計打開煙槍袋,揀出一枝犀角槍,擱在炕上煙盤裡。另外有 一個紫檀木的小方匣子,開了蓋共有三層,每層上是四個煙鬥,三四一十二個煙鬥。伙 計又在一個小口袋裡掏出一個玻璃罐子來,玻璃罐子裡滿滿的盛著一罐子煙泡,伙計們 替他一個一個的上在煙鬥上。這裡叫天兒脫去翎眼貂馬褂,裡面原來穿鹿皮坎肩兒呢。 春大少爺忙著叫家人泡好茶,家人們端上茶來,又擺上許多茶食,紅的綠的,共有十幾 種。叫天兒端起茶來,喝了兩口,便說:「我告罪,要抽兩口。」春大少爺忙說:「請 便!請便!」春大少爺卻不走,一邊坐著陪他。叫天兒躺下去,呼、呼、呼一連抽了七 八口,這才有點精神,一面抽著煙,一面和春大少爺閒談道:「大爺,您去年買的那個 銀合馬,還在那哈兒嗎?」春大少爺道:「喂著呢。」叫天兒道:「腳底下可不錯?」 春大少爺道:「也還下得去。」叫天兒道:「我前兒買了一對醬色騾子,花了四百銀子 ,毛片兒一模一樣,連城根周家那對都趕不上,您明兒瞧著吧!」
叫天兒正在高談闊論,他伙計急得什麼似的,跑進來道:
「老闆,場上餘莊兒唱了一場了,你老扮戲去吧!」叫天兒道:「我知道了。」又 抽了七八口,這才站起身來,對春大少爺道:「我扮戲去了,回來見吧。」春大少爺格 外周旋,又把他送到戲房裡。叫天兒從從容容的扮好,餘莊兒已經下來了。接著《討魚 稅》,外面場上的鼓,打得雨點兒似的,叫天兒才放下京八寸,掛上鬍子,一掀門簾出 去了。春大少爺知道大功告成了。
這時候天黑了,內外點起燈燭,照耀如同白晝。春大少爺出來歸座,一會兒覺得身 上那件海龍馬褂太累贅,便叫:「來啊!」家人們答應著,春大少爺道:「拿那件貂馬 褂上來!」
家人們在衣包裡取了出來,春大少爺換上。這時候叫天兒正唱著《昨夜晚》一段, 台下鴉雀無聲,靜靜的側著耳朵在那裡聽。
唱完這一段,陸大軍機連聲喝采、叫賞。跟班的答應著,便掏出一封銀子,呈上陸 大軍機過目。陸大軍機皺著眉頭道:「這裡才五十兩,太少了!再加一封吧。」跟班的 又掏出一封銀子,兩封一齊扔到台上去,台上出過紅人謝過,陸大軍機便欠身向華尚書 告罪,說:「是要早點回去歇著,怕明兒誤了差。」華尚書不便強留,送了陸大軍機出 去。
回來朝春大少爺一看,便和春大少爺道:「你來,我有話跟你說。」春大少爺摸不 著頭腦,只得跟著他到一間書房裡。
華尚書道:「你這件馬褂,是幾時買的?」春大少爺道:「前兒才買,舅舅看好不 好?」華尚書鼻子裡冷笑一聲,道:「虧你是世家公子哥兒,連這點規矩都不懂!你可 知道,這件馬褂,主子打圍的那一天,才穿上一回。你配嗎?快給我脫下來啵!」
春大少爺羞的滿面通紅,只得把馬褂脫下來。華尚書叫小跟班的進來,吩咐道:「 你到上房裡去,對管衣裳的十九姨奶奶說,把我前兒收拾好的那件甘尖的馬褂拿出來, 請春大爺穿。你把這個帶進去吧。」說完了這句話,便踱出去了。
春大少爺只得在書房裡呆等,等那小跟班把甘尖馬褂拿出來換上,才搭訕著出來。 少時開席,開過席戲也完了,各客俱散。春大少爺無精打采,混出了華尚書的宅,回家 安歇不提。
且說這華尚書名叫華林,是滿洲貴族蘇丸瓜爾佳氏。少年時由一品廕生出身,現任
禮部尚書,在朝裡也是個有名角色。
這日是他散生日,沒有大舉動,不過唱唱戲,請請客罷了,已經鬧得人仰馬翻了。
第二天,到過衙門,又到各處去謝了步。
回到宅裡,門生故舊已經擠滿在書房裡了,華尚書一一接見。
便是部裡的司官,趕來畫稿。諸事完了,快天黑了。華尚書極好的酒量,終日醉鄉 。伺候慣的家人們,便擺上幾種小廚房裡弄的肴饌,捧上酒來。華尚書自斟自酌了一回 。
忽然門上傳進一封信,信上圖書花押重重。華尚書暗自猜疑。拆開信封,上面蓋著 一張小字名片,是薛機。華尚書低頭一想,想起了:薛機是軍機章京達拉密。心裡忐忑 道:「什麼事呢?」再看那信上寫道:
今日周楷遞呈封口折一件,參公賣缺得賄,情節甚重。上意頗怒。公速求陸軍機以 解此圍,否則恐有不測。十二月初八日名叩
閱後付丙。
華尚書看罷,把他酒都嚇醒了,連忙說道: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?」楞了一會,又 想周楷這人名字好熟,想了半天,恍然大悟道:「就是有天在吳侍郎席上,他請教我, 我沒有理會他那個人。這真是杯酒戈矛了!」一面換衣服,一面叫提轎,上陸軍機宅裡 去,求他解圍。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總督受驚惶 入禁省章京逞權力
且說華尚書聽見御史周楷有參他的信處,連夜趕到陸大軍機宅裡,求他轉圜。及至 停下轎來,門口上擋著說:「中堂醉了,請大人明兒來吧。」華尚書再三央告。門口說 :「大人不知道咱們老中堂的脾氣嗎?他喝上酒別的就顧不得了,無論什麼人去見他, 他給你一個糊裡糊塗。他要高起興來,論不定還灌上你幾盅。」
華尚書無奈,只得怏怏的回去。第二天便上去請了三天操,暗地裡托人到大總管那 裡去打點,面子上算是托了陸大軍機。
到底錢可通神,這樣一場大事,大總管不過得了華尚書三千銀子,周楷那個列款糾 參的折子,弄成了個留中不發。華尚書這才把心放下,又去謝過大總管,謝過陸大軍機 。從今以後,也稍為斂跡些,不敢再把他那盛氣凌人的樣子拿出來了。
且說陸大軍機陸穎,號筱鋒,山東濟南府新城縣人氏。二十來歲就進學中舉點翰林 ,好容易熬到開了坊轉了侍郎,又放過一任巡撫。在巡撫任上升了總督。舊年出了個岔 子,著開缺來京,另候簡用。陛見之後,把兩任所得的好處,分了一半,裡頭孝敬大總 管,外面孝敬軍機大臣。不多時候就署了戶部尚書。那時正值人才零替,什麼吳中堂、 呂中堂都病故了,朝廷推算資格,陸穎也是個老人,就下了一道上諭:「陸穎著在軍機 大臣上學習行走。」這一下可跳高了。
但是陸軍機有一種脾氣,叫做嗜酒如命,量又大,誰都喝他不過。北京的風俗,四 月向盡,就要搭上天棚了。他是個大胖子,異常怕熱,四月裡家裡就弄了冰桶,楊梅、 桃子都擱在冰桶裡。每天在軍機處散班之後,回到宅裡,隨意見過幾個客,就在天棚底 下鬧了個獨座兒。伺候他的燙上酒,擺下盤子碟子,他卻正眼也不瞧一瞧,單就著冰楊 梅、冰桃子下酒。喝了四五斤酒,有點意思了,把長袍寬去,再喝下一斤。索性把上身 衣裳寬去,光著脊梁,小辮子繞成一個揪兒。喝到八分醉了,伸手下拉襪子。及至十分 醉了,坐在椅子上,便呼呼的睡著了。
跟班的拿了條毯子,給他輕輕蓋上。這一睡,不知睡到什麼時候,也許晚上一點鍾 ,也許晚上兩點鍾。等到醒了,洗洗臉,漱漱口,飽餐一頓,順便要進內城去了。
且說在軍機處當差,從王大臣起,到章京為止,四更時分一個個都要催齊車馬,趕 進內城去的。章京有值宿的,王大臣總是四更進去。春夏秋三季倒還罷了,最苦的單是 冬天,萬木蕭條,寒風凜冽,便是鐵石人也受不住,何況是養尊處優的那些官兒!單說 這天,陸大軍機酒醒了,跟班們伺候過一頓飯,便出門上車。其時正是隆冬,悠悠揚揚 ,飄下一天大雪。陸大軍機是經慣了,也不甚覺得寒冷;跟班們跨在車沿上,只是瑟瑟 縮縮,抖個不住。及至到了內城城門口,陸大軍機下了車,便有蘇拉接著,提一盞小小 燈籠。這燈籠是葫蘆式,中間圍了一條紅紙,除非軍機處和著兩齋才能有這個燈籠,餘 外都是摸黑摸進去的。
蘇拉在前,陸大軍機在後,一路上也不知踏碎了幾許瓊瑤。
忽然覺著有一個人,氣喘吁吁的追蹤而至。陸大軍機便停了腳步,大聲問道:「你 是誰?」那人低低答道:「兩廣總督馮文毅。」陸大軍機叫蘇拉把燈舉起,細細一照, 只見馮文毅身上拖泥帶水的,不勝詫異。便說:「你跟著來吧。」原來馮文毅那天剛剛 召見,他進了內城門,不知路徑,內城門一轉彎,就是一道御河,這時被雪填滿了,也 看不出什麼河不河,一個不留神,踏了一腳空,便跌向御河裡去了。幸虧一則御河水淺 ,二則御河裡結了一層厚冰,否則要載沉載浮的了。馮文毅把心捺定,摸著一根木樁, 慢慢的把身子掙扎起來,拖泥帶水的上了岸。正苦辨不清路徑,遠遠看見一盞燈籠,把 他喜的什麼似的,放開腳步跟將上去,原來是陸大軍機。當下三人進了西華門,馮文毅 到了朝房,便自踱了進去,伺候召見。
陸大軍機徑奔軍機處。原來軍機處的屋子極像一座對照廳:
一邊是王大臣起坐之處,一邊是達拉密章京跟著那些章京起坐之處。陸大軍機歇息 了一會,上頭叫起,陸大軍機就和一班王大臣進去。等到退下來已經是辰牌時分了。各 軍機回到軍機處,叫達拉密章京進來,今天有幾道什麼上諭,軍機大臣一面說,達拉密 章京一面用手折記清,然後回到自己的那間房子裡去分派擬稿:某某兄擬哪一道,某某 兄擬哪一道,一霎時筆如風雨。
達拉密章京看過了,又斟酌幾個字,然後拿給軍機大臣看。軍機大臣裡面,有兩個 滿洲人,文理都不甚通透的,還得漢軍機細細的講給他聽。大家以為可用,就發下去, 叫蘇拉謄清了,送到上頭去。送上去的時候,蘇拉和太監都不准講話,單是提著氣,在 嘴裡呼的一聲。太監知道了,拿了上去。少停,拿出來交給蘇拉。蘇拉回到軍機處,那 底稿後面有了個指甲印的,便已蒙上頭允准了,然後發出去,頒行天下。這裡王大臣各 各退班,陸大軍機最性急,總是頭一個走。達拉密章京看見王大臣走了,他也照樣,除 掉那幾個值宿的不能離開一步,其餘也都溜之乎也。值宿的是兩個人一夜,像輪缺一樣 ,個個要輪到的。不過到了輪著某人的那一夜,某人有事,可以托朋友替代,不必限定 是要原人的。在內值宿的,也無他苦,只是淒涼寂寞罷了。那夜還有半桌酒席,有樣攤 黃菜,外頭是做不來的,這都不在話下。
再說軍機章京裡面,分為兩班:一班是漢章京,一班是滿章京。漢章京有五個字的 口號,叫貂、珠、紅、葫、熏:貂,是貂褂,每年立冬,軍機處、南書房、如意館、太 醫院,上頭都有得賞下來的;珠,是朝珠;紅,是紅車沿;葫,是葫蘆燈;熏,是熏人 。滿章京也有五個字的口號,叫做吃、著、困、躺、戤:吃,是吃飯;著,是著衣;困 ,是困在牀上;躺,是躺在椅子上;戤,是戤在牆頭上。漢章京跑得精光了,他們還沒 有散,這是什麼緣故呢?他們原來想把幾條不要緊的上諭出去熏人。看看日色平西了, 滿章京就發急了,口中混帳王八蛋的把蘇拉大罵,叫他去鈔上諭。蘇拉說:「我的老爺 ,上頭還沒下來呢,你叫我到哪裡去鈔呢?」滿章京更發急,連連跺著腳說:
「瞧這是什麼時候了,上諭還沒有下來,你想賺誰!真有你們這班混帳王八蛋!」 蘇拉被他罵不過了,只得走過去,把那不打緊的鈔個一兩條給他,而且寫得潦潦草草, 歪歪斜斜,有幾位認不大真的,還左一安,右一安,央告同班的人把認不真的字,一個 個用恭楷注在旁邊。這才一哄而散。
同是一樣的章京名目,這樣一看,真真是分隔雲泥了。並不是漢章京裡面都是精明 能乾的,滿章京裡面都是昏聵糊塗的。
不過滿人裡面,唸書的太少,他們仗著有錢糧吃,仕途又來得比漢人寬,所以十成 裡頭,倒有九成不唸書的。朝廷滿漢並用,既有了什麼官什麼官的名目,就是不行也只 好拿來將就將就、搪塞搪塞了。漢章京裡面也有些不行的,達拉密章京了然於胸,有些 事情都不去驚動他,到了忙的時候,把批好的折子,什麼「知道了」,「該部議奏」, 都一條一條的夾在折子裡面,叫他用漿糊一條一條的黏上去就是了。這又叫做「麵糊章 京」。
看官,這並不是做書的挖苦他們,實實在在有這麼一回事。正是:
賢愚分兩等,高下集群材。
一入軍機處,青雲足底來!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機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
上回書說了軍機的樂處,如今再說軍機苦處。有個御史叫做汪占元,是浙江人氏, 有天要遞個折子,那時老佛爺已住在園子裡去。這個園子在西直門外,單有一條大路, 直接這園子,兩旁都是參天老樹夾著桃李梅杏,又有許多楊柳。到得春天,紅是紅,綠 是綠,真是天然圖畫。那時堅冰未解,地凍天寒,一路上不過枯木椏槎而已。汪御史坐 上車子,出了西直門,徑奔園子而來。那刮面尖風常常從車帷子裡透進來,汪御史雖穿 了重裘,也不禁肌膚起粟。及至到得園門口,汪御史下來了,趕車的把車拉過一旁。汪 御史整了整衣冠,兩手高擎折盒。進了園門之後,一直甬道,有座九間廣殿。這廣殿正 門閉著,旁門開著。汪御史由旁門進去,到了奏事處,口稱:「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汪占 元,遞奏封事一件。」隨即在台階底下跪了下去。
值日太監接了盒過去。汪御史朝上磕了三個頭,站起身來,退了三步,一直走出來 。
這才留心四望。只見奏事處對過有三間抱廈,窗櫺上糊的紙已經破得不像樣子了, 門上用紅紙條貼了三個字,是「軍機處」。汪御史心上一凜,曉得擅進軍機處,無論什 麼皇親國戚都要問斬罪的,因偷偷的立在抱廈外面,仔細端詳。只見裡面共是三間:一 間做了軍機處王大臣起居之所;一間裡面有幾副板牀,都是白木的,連油漆都不油漆, 擺著幾副鋪蓋,想是值宿章京的了;那一間不用說,是達拉密章京及閒散章京起居之所 了。心中暗暗歎道:「原來軍機大臣的起居不過如此!」
園裡雖說是森嚴禁地,有些做小買賣的也可隨意進來。太監們及有宮門執事的,為 著就食便當,所以不肯十分攆逐。看官們試想想,那些做小買賣的有什麼斯斯文文的, 自然是嚷成一片。少時,看見兩個蘇拉,戴著紅帽子,跑出來高聲說道:
「王爺、中堂們為著你們這兒鬧不過,叫你們一起滾出去。要不然,要送你們到衙 門裡去打板子了。」說罷,有一個蘇拉手裡拿著根馬鞭子,在那裡劈頭劈臉的亂打。那 些做小買賣的,一霎時哄然四散,卻都閃在樹底下或是牆邊,都不肯走開去。
汪御史不知他們是什麼意思。少時,見他們又漸漸圍攏來了。
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歎道:「原來軍機大臣的威權,不過如此!」
少時,太陽漸漸的直了,蘇拉們都一個個跑到小吃擔子上買東西吃。有兩個給錢給 少的,拉住了袖子不肯放他走的;有的把碗端了過去,錢也不給碗也不給,賣吃的人在 那裡叫罵的,一時不能盡述。少時,一個紅頂花翎的慢吞吞的走出來,巴著門兒,對那 賣冰糖葫蘆的招手。汪御史細細的一看,原來是陸大軍機。只見賣冰糖葫蘆的把一串冰 糖葫蘆遞在陸大軍機手裡。
陸大軍機在身上掏出幾個錢來,給賣冰糖葫蘆的。看他拿著一串冰糖葫蘆,回過頭 來四邊一望,早已三腳兩步的跨進軍機處去了。又是一個蘇拉,拿著銅錢在手心里數, 又掉了兩個,毛腰撿起,跑到賣粢團的擔上買了兩個粢團,嘴裡還說:「你多擱糖,這 是裡頭孫中堂吃的。」旁邊又一個蘇拉說道:「他一把的年紀,吃這個黏膩東西,回來 不怕停食嗎?」買粢團的蘇拉道:「麻花他又嚼不動,還是這個爛些。他現在餓的慌, 停食不停食也就不能管了。」說著,托了粢團去了。汪御史心中又暗暗的歎道:「原來 軍機大臣的飯食不過如此!」
一會兒,又是兩個蘇拉嘻嘻哈哈的在汪御史面前走過,一頭走一頭說道:「老塔呀 ,你剛才沒有聽見王爺埋怨孫中堂嗎?」那個蘇拉說:「為什麼事情要埋怨他呢?」說 是:「他上去的時候,有樁事回錯了話,碰了釘子下來,又給王爺埋怨了一場,你不看 他臉上那種怪不好意思的樣子……」以下走遠了聽不清楚。汪御史心中又暗暗歎道:「 原來軍機大臣的榮耀不過如此!」
心裡一頭想,不知不覺的走了出來。走到園門口,看見侍衛們在那裡閒談,一個道 :「老玉,咱們那哈東頭,開了座羊肉舖子,好齊整的餡子!咱們明兒在那裡鬧一壺吧 。」那個叼著小煙袋,一聲不言語,這個就說:「你放心啊,不吃你的。」
那人方才把小煙袋攥在手裡,在牙齒縫裡迸出一口唾沫,吐在地下,說:「那倒不 在乎此!」汪御史搶前了幾步,那邊又有兩個侍衛在那裡敬鼻煙呢。這個接過來,且不 聞煙,把個炮針筒的磁壺翻來覆去,說:「這是寒江獨釣,可惜是右釣;要是左釣,就 值了錢了。」
說完了這句,把煙磕了點在手心裡,用指頭黏著,望鼻子管裡送,接連便是幾個噴 嚏。那個哈哈大笑道:「你算了吧!
回來嗆了肺,沒有地方貼膏藥。」那個把壺遞過去,嘴裡還說:
「好傢伙,好傢伙!包管是二百一包!」汪御史又搶前了幾步,便到空場上。跟班 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。汪御史走過去,跟班的服侍著主人上了車,自己跨上車沿子。 趕車的把鞭子一揮,那車便望來的那條路上,滔滔的去了。
汪御史在車子裡,心中感歎道:「方才看見軍機大臣的樣子,令我功名之念登時瓦 解冰銷!」正在出神,車子已進了西直門,趕車的便問:「爺要上什麼地方去?還是回 家?」汪御史道:「我要到浙江會館去拜個客。」趕車的聽了,便把車子望東趕去。不 上二三里,就是正陽門。正陽門一條大路,車馬往來,自朝至暮,紛紛不絕。汪御史在 車子裡忽然覺得車輪停了。探出頭來一望,原來是叉車。後來愈來愈多,把一條大路擠 得水泄不通。汪御史十分著急。看見人家也有下車來買燒餅吃的,也有在車廂裡抽出書 來看的,也有扯過馬褥子來蓋著睡覺的,無不神閒氣靜,汪御史也只得把心捺定了,在 車裡呆呆的等。等到太陽沒有了,方才漸漸的疏通。汪御史看時候遲了,客也來不及拜 了,便說:「回去吧。」
趕車的把車趕到家門口,汪御史進去了,脫去衣冠,太太便同他說道:「今天煤沒 了,米也完了,跟班的和老媽子要支工錢。你明天要打算打算才好!」汪御史聽了,異 常愁悶,便道:「太太,我何嘗不打算?偌大京城地面,像我們這麼樣的官兒,正不知 論千論萬。照這樣一年一年熬下去,實在有點煩難。就是我同衙門的幾位,光景和我不 相上下,除掉賣折子得那幾個斷命錢之外,還有什麼意外出息麼?」兩人說著,又相對 唏噓了半日。太太忽然想起道:「你不是前天說,你有個堂房兄弟,進京引見來了?他 是個闊人兒,可有什麼法子弄他幾個?」汪御史搖頭道:「那是我一脈之親,怎麼好意 思去想他的錢財呢?」太太道:「現在家裡這個樣子,年又來了,也叫無可奈何了!」 當夜無話。
次日,汪御史便去找那個堂房兄弟。他堂房兄弟叫做汪占魁,很有家財,在杭州城 裡專事遊蕩。他父親愁的了不得,看看他年紀大了,什麼事不能做,還是替他捐上一個 官,雖不望他耀祖榮宗,也給他留下一個衣食飯碗。那年秋裡黃河決口,急待賑捐,到 處遍設了局子,只要七成上兑。他可就花了五千銀子,給汪占魁捐了個大八成知縣。這 回進京引見,嫌店裡嘈雜,借住在一個人家。這個人家,是在京裡當書辦的,有個親戚 在杭州織造那裡當茶房,不知如何被他認得,此番與汪占魁結伴來京,汪占魁就住在他 家裡。臨行時,他父親給他一封信,說:「京城裡有你堂房哥子在那裡做御史,一切事 體托他,諒無不妥的。」他到京之後,到汪御史家投信,汪御史剛剛拜客去了,不曾會 著。他因為著居停主人連日替他擺酒接風,忙得不亦樂乎,也不曾到汪御史家裡去過第 二遭。這天,剛剛起身梳洗,外面傳進一張片子,他一瞧是堂房哥子來了,連忙叫「請 」。
欲知汪御史見了汪占魁面後,有什麼說話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八回 急告幫窮員謀卒歲 濫擺闊敗子快遊春
且說汪御史的兄弟,自得杭州織造家人介紹,認識一個書辦,到京之後,就住在書
辦家裡。連日狂嫖濫賭,樂不可支。
這天汪御史前去看他,他卻坦然高臥。及至家人把他搖醒了,他才慢慢的披著衣裳
起來,趿著鞋子,踢達踢達的趕到前廳。
汪御史已經等的不耐煩了。二人見面之後,少不得談些家鄉的故事。他兄弟舉目一 看,只見汪御史這樣冷的天氣,還穿著一件舊棉袍,上頭套了一件天青哈喇呢的羊皮對 襟馬褂,棉袍子上卻套著雙沒有槍毛的海虎袖頭,心中十分詫異。
少時那書辦出來相見,請教名姓,方知姓尹名仁,是直隸人,在吏部有二十多年了 。衣服倒也樸實,只是生了一雙狗眼,幾撇鼠須。汪御史少不得周旋他兩句,說:「舍 弟在尊府上打擾,不安得很!」那些套話。尹仁便呲牙裂嘴的說道:「汪老爺,您別鬧 啦!令弟二爺既和咱盟兄周老壽要好,就跟咱要好一樣。舍下有的是房子,只是三餐茶 飯,沒有什麼好東西吃罷了!」說罷,哈哈大笑。一會兒又說道:「現在已經是晌午了 ,汪老爺住的老遠,趕回去怕府上的飯已經吃過。不知道可肯賞臉,就著舍下的破碗兒 破碟兒,吃一頓窮飯?」汪御史看這人語言無味,面目可憎,本來想辭他的,只是肚子 不爭氣,咕嚕咕嚕的叫起來了。當下只得連說:「客氣,客氣!奉擾就是了!」尹仁聽 了,便喊:「來啊!」有兩個小子跑了出來,尹仁對他們嘁嘁喳喳的一陣,兩個小子又 跑進去了。一會兒用一個木盤先端出茶來,尹仁敬了汪御史,然後又敬汪御史的兄弟, 臨了自己拿了一杯。尹仁一面喝著茶,一面兩個眼珠子望著茶在那裡發怔,像是想什麼 心思似的。汪御史看他這個樣子,便拉著他兄弟問長問短。他兄弟才把要捐官的事一一 告訴了汪御史。
汪御史想道:「怪不得尹書辦這樣款待他,原來他想賺這注上兑的扣頭呢!」
正在狐疑,又聽見碗盞丁當之聲,兩個小子早搬飯出來了。
一面調排座位:自然是汪御史首座,他兄弟二座,尹仁下陪。
汪御史舉目看那菜時,十分豐盛,方明白剛才尹仁嘁喳了一陣,是叫小子到廚房裡 去多添幾樣肴饌出來的緣故。一時飯畢,又漱過了口,心裡想和他兄弟借個一百五十兩 。一想第一回見面,到底有些不好意思;想著昨天太太同他說的家裡窘迫情形,實在挨 不過,只得硬了頭皮走過去,把他兄弟拉了一把。他兄弟會意,便走到一間套房裡,汪 御史跟著進去。兩人坐定了,汪御史湊著他耳朵,說道:「論理呢,我不應該同你老弟 開口,爭奈愚兄實在迫不及待了,所以只好同你老弟商量,借個一百金,或是二百金, 過了年,有別處的錢下來,先把來還你。」
他兄弟聽了,心裡一個鶻突,想:「我們老兄在京城裡做官,做了這許多年,難道 一個錢都沒有剩,窮到這樣?臨行時節,家裡上人交代過的,一切事都要他照應。他如 今既和我開口,我要不應酬他,似乎於面子上過不去。」便滿口答應道:「有,有,有 !」一頭說,一頭直著嗓子喊道:「老尹呀,老尹呀!」
尹仁急急忙忙的走進來道:「二爺什麼事?」他道:「我昨兒存在你那裡的一封銀 子,你給我拿過來,我有用場。」尹仁看了他一眼,又看了汪御史一眼,方才走出去。 少刻捧了一封銀子過來,說:「你可自己點點數目,對不對。」他一手搶過來道:「算 了啵!你也會錯嗎!」他跟手把一封銀子打開了,數了數,整整的一百兩。對汪御史道 :「大哥,你先拿去使,要不夠,我還替你籌畫。」尹仁在旁邊聽了這兩句話,不覺的 微微笑了一笑。汪御史羞的臉紅過耳,忙把銀子揣在懷裡,把手一拱,說聲「多謝。」 匆匆而去。
他兄弟送到大門口,尹仁也跟著出來,彼此彎了彎腰,汪御史上車走了,他們倆方 才進去。尹仁不禁歎了一口氣道:「難啊,難啊!」汪老二道:「你說什麼?」尹仁道 :「我就說你們這位堂房令兄,他還算是好的。有些窮都窮到腿沒褲子的都有!」汪老 二聽了,又十分詫異。尹仁說:「你怎麼把那封銀子全給了他?」汪老二道:「怎麼不 全給他?一起只有一百兩銀子,牌算什麼事!咱們昨兒打一百銀子一底二四的麻雀牌, 我一副不就贏了六十兩;只要今兒出去,再和上兩副三百和,他借去的這一百兩,就有 在裡頭了。」尹仁道:「不錯,不錯,借給了他,就跟輸掉一樣。你譬如給人家敲了一 副莊吧!」
兩人說說笑笑,不知不覺,已是四點鍾時候了,尹仁道:
「你今兒還出去不出去?」汪老二道:「怎麼不出去!昨兒不是在順林兒那裡,許 他今天吃個飯嗎?你先答應了,我才允他,你現在又裝起糊塗來了,可是開我的玩笑? 」尹仁道:「哦,哦,哦。是的,是的。我真該死,我真該死!」又道:「你坐了我的 車去吧,回來我來找你。」汪老二道:「你自己怎樣?」
尹仁道:「說不得,拿鴨子了!」汪老二皺著眉頭道:「這個我心裡怎麼過意得去 呢?」尹仁道:「你別裝腔了,老實的坐我的車吧!你要心裡過意不去,多請我吃幾回 相公飯,那就補報了我了。」汪老二道:「何消說得!」一面汪老二上樓去換衣服,一 面尹仁叫小子喊趕車的套車,伺候汪二爺出去,自己便揚長走了。
汪老二換過一身時新衣服,拿鏡子照了又照,方才停當。
出得尹家門,坐上車,趕車的問:「二爺上哪裡?」汪老二道:
「韓家潭。」趕車的知道他去逛相公窯子,不是喝酒就是吃飯,又有車錢到手了, 便格外起勁,鞭子一灑,那施車的牲口如飛而去。不多一會,到了韓家潭,找著了安華 堂的條子,下了車。
車夫用手去敲門,那門呀的一聲開了,走出一個跟兔,問:「爺是哪裡來的?」汪
老二說了一遍。跟兔說:「請裡面屋子裡坐。」
汪老二進了大門之後,細細的看了一遍。只見進了大門之後,便是一個院子。院子
裡編著兩個青籬,籬內尚有些殘菊。
有一株天竹累累結子,就如珊瑚豆一般鮮紅可愛。一株臘梅樹開滿了花,香氣一陣 陣鑽進鼻孔裡來。上了台階,跟兔在外面說了聲:「有客!」裡面有人便把簾子打起來 。汪老二一看,原來是一排三間,兩明一暗,兩邊都有套房。正中那間屋子裡擺了一張 炕牀,炕牀上一隻天然幾,供著瓶爐三事。兩邊八把紅木椅子,四個紅木茶几。汪老二 站定了,跟兔說:「請老爺書房裡坐。」便掀起一個白綾淡水墨的門簾。
到了裡邊,汪老二隨意在一把楠木眉公椅上坐下,四面一看:身後擺著博古櫥,櫥 裡擺著各式古董,什麼銅器、玉器、磁器,紅紅綠綠煞是好看。壁上掛著泥金箋對,寫 的龍蛇夭矯,再看下款是溥華。汪老二知道這溥華是現在軍機大臣。又是四條泥金條幅 ,寫的很娟秀的小楷,都是什麼居士、什麼主人,底下圖章也有乙未榜眼的,也有辛巳 傳臚的,還有一位,底下圖章是南齋供奉,便知這些都是翰林院裡的老先生。跟兔早把 紫檀茶盤托了茶來,是淨白的官窯。汪老二揭開蓋,碧綠的茶葉,汪老二是杭州人,知 道是大葉龍井,很難得的。細細的品了一回,又問:「這水是什麼水?」跟兔說:「這 是玉泉的泉水。」汪老二點頭贊歎。
忽然門簾一啟,一個美少年走了進來。頭上拉虎貂帽,身上全鹿皮做的坎肩兒,下 面是駝色庫緞白狐袍,腳上登著漳絨靴子,原來就是順林兒。順林兒對著汪老二把腿略 彎了彎,算是請安了,汪老二已是喜形於色。順林兒又奉承了他幾句,汪老二更是心花 怒放。隨即叫拿紅紙片,跟兔答應著送上一疊紅紙片。汪老二走到書案邊一張樹根獨座 上坐好了,順林兒便來磨墨。汪老二連忙止住他道:「你別髒了手。」順林兒笑道:
「不妨事的。」汪老二寫了幾個客:什麼西單牌樓張兆璜張老爺,南橫街李繼善李 老爺,爛面衚衕周繩武周老爺,還有浙江會館兩個同鄉,一個姓王,叫做王霸丹,一個 姓胡,叫做胡麗井。汪老二寫畢,叫跟兔的拿出去,速速打發分頭去請。正在忙亂的時 刻,門簾外突然鑽進一個人來。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二十九回 坐華筵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聽雞鳴
且說汪老二在韓家潭順林兒家請客,正在拿紅紙片寫條兒的時候,門簾外鑽進一個 人來。汪老二定睛一看,原來是尹仁,連忙起身讓坐。尹仁坐下,順林過來招呼了幾句 ,便走出去了。
這裡汪老二便和尹仁到套間裡那對嵌螺甸紅木小榻牀上,叫跟兔拾掇煙槍。汪老二 並不抽煙,不過借此躺躺罷了。尹仁卻是大癮,每天要抽一兩多,抽的臉上變做鐵青色 了。當下二人對面倒下,尹仁也顧不得說話,一上手,颼、颼、颼就是十幾筒,這才和 汪老二說話。
一會兒順林出條子去了,有兩個徒弟,一個叫做天喜,一個叫做天壽,走進來伺候 他們。天喜便爬在炕上,替尹大爺燒煙;天壽無事,幫著上鬥腳紗。汪老二看那兩個小 孩子生得也還清秀,便問他二人是哪裡人。天喜說是揚州人,天壽說是蘇州人。汪老二 又問他們現在學了幾齣戲,再過幾年可以滿師,二人一一回答了。
看看金烏西墜,玉兔東升,外面跟兔嚷聲「客來!」汪老二連忙爬起一看,是王霸 丹和著胡麗井,二人都是猞猁猻袍子,戴著熏貂皮困秋。彼此作過揖,尹仁才慢慢從榻 牀上爬起來,與他們廝見。他們和尹仁是熟朋友,向來玩笑慣的。尹仁看見胡麗井鈕釦 上掛著赤金剔牙杖,手上套著金珀班指,腰裡掛著表褡褳、象牙京八寸、檳榔荷包、翡 翠墜件兒;一擄袖子,一隻羊脂底硃砂紅的漢玉金剛箍,這箍要值好多銀子,便皺著眉 頭,對胡麗井道:「老麗呀,你要打架可不了!」胡麗井道:
「你瞧見我和誰打架來?」尹仁道:「別認真,我不過這樣說罷了!」大家哈哈一 笑。回頭再看王霸丹,身上一切著實鮮明,就是底下趿著雙毛窩子。尹仁又道:「老八 ,你穿著這就出來了麼?」王霸丹道:「我為著它很舒服,所以懶得換了。」尹仁道: 「你圖舒服,那還是蒲鞋。」王霸丹道:「你別耍你那貧嘴了,瞧瞧你自己吧!」尹仁 道:「我自己沒有什麼呀,不過這件繭綢袍子,配不上你那個猞猁猻就是了。」王霸丹 道:
「要拿好的衣裳望你身上擱,也稱不起你那腦袋。」尹仁道:「我這腦袋還推板嗎 ?」胡麗井在旁插嘴道:「這可成了蝦蟆跳在戥盤子裡,自稱自贊了。」
三人說說笑笑,還不見張兆璜、李繼善、周繩武三人到來。
把他們等得不耐煩。問問催客的,說是:「統統知道了。」良久,良久,李繼善來 了,張兆璜、周繩武尚無影響。汪老二在身上摸出表來一看,已經八點多種了。李繼善 說:「我們擺吧。兄弟今夜要早回去,明天有事。」汪老二無法,便道:「也好,我們 吃著等。」一面招呼跟兔的端整酒菜,一面又叫拿花紙片,請各人叫條子。尹仁頭一個 高興,把筆搶在手中,說:「我來寫。」李繼善說:「我叫琴儂。」於是王霸丹叫紅喜 ,胡麗井叫二奎,落後尹仁自己寫了個綺芝。一共四張條子發了下去。
打雜的端上盤碗,早有人把檯子搭開。等到杯筷上來,安排停妥,天喜在旁邊便叫 拿邊果。這邊果就是瓜子。眾人相讓入座,自然是李繼善首座,又單單留了二座、三座 給張兆璜、周繩武,胡麗井坐了第四位,王霸丹坐了第五位,尹仁與汪老二擠在底下做 陪。這時候順林已經回來了,便上前斟過一巡酒,先生在門外拉動胡琴,順林唱了一折 《桑園會》的青衫子,大家喝采。相公飯的酒菜向來講究的,雖在隆冬時候,新鮮物事 無一不全,什麼鮮茄子煨雞、鮮辣椒炒肉這些鮮貨,都是在地窯子裡窯著的。眾人吃著 ,贊不絕口。還有一樣蝦子,拿上來用一隻磁盆扣著,及至揭開蓋,那蝦子還亂蹦亂跳 ,把它夾著,用麻油醬油蘸著,往口裡送。尹仁說:「你們別粗魯!仔細吃到肚子裡去 ,它在裡面翻筋斗,豎蜻蜒,像《西遊記》上孫行者鑽到大鵬金翅鳥肚子裡去一樣,那 可不是玩兒的!」眾人大笑。順林便擰了他一把道:「你又在那裡胡說八道了!」
吃不到一半,胡麗井的二奎來了。尹仁便拍手道:「恭喜,恭喜!打著了頭彩了! 」胡麗井面上也很得意。少時,綺芝、紅喜都陸續來了,惟有李繼善的琴儂沒有來。李 繼善忽忽如有所失,面上更露著一種慚愧之色,便道:「這王八蛋真可惡,他裝紅!順 林道:「你別怪他,他今兒可真忙!」李繼善方才不語。忽地跟兔一掀簾子,衝著李繼 善說:「老爺的條子到!」
眾人回頭一看,只見琴儂穿著倭刀馬褂,款步而來,但是身軀肥胖,一雙眼睛又是 蘿蔔花,汪老二心中暗暗的好笑。見他望李繼善旁邊兒一坐,一聲不言語。李繼善便咕 嚕道:「好大的架子!」琴儂不聽猶可,聽了之後,焱欠地立起身來,說:「得罪了, 我要上天和堂去!」說罷就走,也不招呼李繼善。李繼善這一怒非同小可,登時嚷道: 「好王八蛋!明兒送他!」
順林勸道:「他是小孩子。李老爺,你何苦跟他一般見識!」
李繼善也無顏再坐,只得訕訕的告辭走了。汪老二送過,回到屋子裡,說:「琴儂 今兒怎麼發起標來?」順林道:「不怪琴儂。李老爺先前叫過十幾個條子,半個大錢沒 有給。他今天來了,沒有問他要帳,還算是好的!」眾人方才恍然。
這裡胡麗井、王霸丹揮拳鬧酒,鬧到三更多天。汪老二道:
「我也乏了,讓我歇歇吧!」胡麗井、王霸丹方才罷手。一同用過稀飯,盥漱過了 。胡麗井、王霸丹同叫套車,汪老二攔住他們道:「你們回到會館裡去睡覺也怪悶的, 不如咱們來打小牌吧。」胡、王二人道:「有理,有理!」於是重新坐下,彼此談天, 一面又催尹仁快過癮。他們談天的當口,打雜的早把殘席撤去,泡上上好的茶來。四人 喝著,尹仁又抽了十幾筒煙,這才精神奕奕。順林兒叫天喜進去,拿麻雀牌和籌碼,一 面在套間那張紅木小檯子上點上四支洋蠟,照得通明雪亮。順林替他們分好了籌碼,叫 天喜、天壽好好伺候著:「我告假。」說著進裡邊去了。
這裡四人扳位就座,尹仁便問:「我們打多少底?」汪老二道:「你怪煩絮的,一 百塊底么二就是了。」胡、王二人還嫌大,汪老二道:「算了罷,這還嫌大,已經再小 沒有了!」
胡王二人只得勉強答應。四人打了兩圈莊,沒有什麼大輸贏。
剛剛到得第三圈,順林出來了,坐在汪老二身後。汪老二和他鬼混著,也不顧手內 的牌了。不提防對家胡麗井中風一碰,發風一碰,自摸一索麻雀,三翻牌攤了下來了。 一數是中風四和,發風四和,自摸一索麻雀十四和,二十二和起翻,一翻四十四,兩翻 八十八,三翻一百七十六。汪老二正是莊家,應該雙倍輸,足足三十五塊二角。汪老二 卻毫不介意,尹仁也聲色不動,只有王霸丹便嚷道:「老二,你真正害人不淺!」汪老 二道:「與我什麼相干?」王霸丹道:「這中風、發風不都是你打的麼?」汪老二愕然 道:「怎都是我打的?」王霸丹嚷道:「奇!奇!不是你打的,是誰打的?」汪老二細 細一想,笑道:「不錯,不錯。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」王霸丹嚷道:「你固然不要緊 ,我們都得輸十七塊六角一家哩!」汪老二道:「老尹不是一樣的陪你輸麼?他卻一聲 不言語。你這樣喉急,不怕他笑你麼?」
王霸丹方始無言。又說:「你叫順林打幾副吧,等你靜靜心再來。再要這樣不顧人
家死活,我們的帳都要你一個人認的。」
汪老二道:「也是,也是!」便讓順林坐下,自己躺在煙榻上,一會兒便朦朧睡著
了。
順林叫天喜到裡面問師娘要件狐皮一口鍾來,替汪二爺蓋著,回頭省得涼了他。直 到又扳過了位,打完八圈莊,天色漸漸的明了,方才把汪老二推醒。汪老二揉揉眼睛坐 起來,跟兔絞上手巾,汪老二揩過,便問:「怎麼樣了?」順林道:「替你輸掉了一底 半。」汪老二道:「有限得很。」掏出靴頁,拿出一張一百塊的票子,一張五十塊的票 子,說:「你們拿去分吧。」三人中尹仁本是大贏家,贏了一百塊;胡麗井贏了三十塊 ,王霸丹贏了二十塊。三人分完了,尹仁因為自己是大贏家,便給了屋子裡人二十塊。 順林替他們謝過了,打雜的端上稀飯,眾人吃過,方才各自出門。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
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祿堂 栽筋斗復試保和殿
卻說汪老二在順林兒家擺飯,飯後約了三人打了一場麻雀。
直到天明,算過輸贏帳,伺候人搬上稀飯,大家用畢。胡麗井等紛紛告辭而去。汪 老二在身上摸出一隻打璜金錶一看,已經到七點鍾了。汪老二連說:「遲了!」便提了 他那條賣估衣的嗓子,叫聲「套車!」外面答應一聲「嗻!」汪老二站起身來整理衣服 ,順林兒忙著上來去替他穿馬褂,扣鈕子。汪老二整理衣服已畢,便說:「我走了。」 邁步跨出房門,順林兒在後相送,一面緊握著他的手說:「您今兒總得來一趟。」汪老 二諾諾連聲。順林兒看他上了車,方才關門進去不提。
且說汪老二回到尹家,已經九點多鍾了。上了樓,倒頭就睡。睡到天快黑了方才起 來。尹家送上晚飯,汪老二吃過,便問伺候人道:「你家老爺呢?」伺候人回道:「老 爺上天祿堂去了。」汪老二道:「是人請他呢?還是他請人呢?」伺候人回稱:「人請 他。就是前面衚衕裡的戶部劉四爺。」汪老二道:
「不是常常跟你們老爺在一塊的劉理台劉四爺嗎?」伺候人回道:「正是。」汪老 二說:「我也請過他好幾趟,今兒他請客不請我!我去闖席,看他怎樣!」說罷,便換 了衣服,坐車直奔天祿堂。在櫃上問明白了戶部劉宅定的第六座,一直從堂裡走進去, 拐個彎兒就是了。汪老二依言往裡直闖,其時已有六點多鍾了,正值上市,滿院都是弦 管之聲,夾著大鼓書、二簧京調。汪老二尋著了第六座,跑堂的嚷聲「客來!」裡面有 人打起門簾。汪老二定睛一觀:一面坐著兩位年輕的,面貌約摸是南邊人,橫頭坐著尹 仁,底下坐著主人劉理台。
汪老二便嚷進去道:「劉四爺,您好呀!您請客,不找我!」劉理台聽得聲音熟, 回過頭來一看,也嚷道:「了不得了!老二找了來了!」汪老二接著說道:「你為什麼 這樣失驚打怪!怕我吃了你的心疼嗎?」劉理台一面讓坐,一面罵家人,說;「剛才叫 你們去請汪二爺,你們說汪二爺一早出門了。原來是你們躲懶,編著話兒哄我,明兒一 個個和我滾蛋!」汪老二忙解說道:「我雖沒有一早出門,可是起來得不多一會。或者 是我的底下人知道我睡的正濃,不敢上來回,所以隨口說了句一早出門,叫你死了心, 別讓他倆再跑腿,也是有的。如今瞧我面上,恕了他們倆吧。」劉理台這才收蓬。
汪老二說話的前頭,尹仁和那兩個年輕的,都和他招呼過了。坐下了,便先請教兩 位年輕的尊姓大名。二人囁嚅了一句,汪老二聽不清楚。劉理台便告訴他道:「他們是 哥兒倆,一位叫做江文波,一位叫做江澄波,江南鎮江府丹陽縣人,是上京裡來會試的 兩位舉人老爺。」汪老二記在心裡。少不得江文波、江澄波也要問他的名姓籍貫。汪老 二一一回答了。主人斟過酒,便讓汪老二再要一個菜。這是北京的風氣,凡客人後到, 席上已要過菜了,總得讓這個後到的客人另外要一個菜,以示恭敬。
閒話休提。再說汪老二隨便要了一個菜,便嚷著要叫條子。
尹仁抿著嘴笑道:「你別叫了,一會兒就來,馬上快!」汪老二詫異道:「怎麼說 ?」劉理台見尹仁業經把那一重公案揭破,當下便站起來深深一揖,道:「大哥,你老 人家總得恕我兄弟的罪!」汪老二更詫異道:「你不說我還明白,你一說我更糊塗了! 」尹仁這才告訴他道:「他那天在你席上看見了順林兒,他賞識了他,叫了他幾個條子 了。今天這局所以不曾約你,是怕吃醋,並不為別。他剛才看見了你,就嚷『汪老二來 了,這可了不得了!』名堂叫賊人心虛。」說到這裡,劉理台在尹仁肩上拍了一下道: 「你才是賊人心虛呢!」尹仁道:「我好好的替你在這兒打圓場,你不謝,還來拍我一 下!我要是加上兩句火上添油的話,汪老二不通你的刀子,算你天月二德!」劉理台道 :「自己弟兄,好意思嗎?」尹仁還說了一句道:「那倒論不定。」一席話說得汪老二 開口不得,心裡暗想:「這是劉理台割我的靴腰子,今天被我撞著,我倒要瞧瞧他倆的 神情!」嘴裡便說:「理哥,你太小心了!叫個條子算什麼事,也值得請安作揖!你還 怕我跟你鬧醋勁嗎?我說句老實話,要是一個相公認定一個老鬥;一個老鬥能夠在他身 上花多少?他家上上下下幾十口子人,不要喝西風麼?」尹仁接著笑道:「好一個寬洪 大量的汪二爺!這才真真夠朋友呢!」
說話之間,順林兒已到,一掀簾子,驟見了汪老二,便一聲兒不言語,在汪老二旁 邊一坐。尹仁拿筷子敲著桌子叫好,劉理台渾身不得勁兒。順林兒坐了坐,便向汪老二 告假,說:
「我今兒還要上絢華堂去,二爺您原諒吧。」說著就走,卻扭過頭來,朝著劉理台 一笑,劉理台至此方才六脈調和。順林兒這番做作,汪老二把方才那些意見,早已渙然 冰釋。以後陸陸續續有兩個小相公來到,是尹仁叫的,唱了一兩支曲子,告假去了。汪 老二再看那江家兄弟,酒也不喝,菜也不吃,盡著對了他們呆呆的瞧著。汪老二和他們 攀談幾句,又吞吞吐吐的一口丹陽話。汪老二聽了,甚是氣悶。尹仁見席間不甚熱鬧, 便道:「我來扌害兩拳吧!」劉理台道:「甚好!」尹仁便和汪老二先扌害了一個「三 拳兩勝」。挨次到江家兄弟。江家兄弟拿手按著杯子,推說不會呷燒刀。尹仁說:「那 就是黃酒吧。」
江家兄弟十分無奈,每人乾了一小杯作為過關。尹仁又和主人劉理台扌害了十拳, 看看天已不早,便叫拿稀飯。大家用畢,謝過主人劉理台,紛紛各散。汪老二自和尹仁 同車回去。
這裡江氏弟兄帶了一個暫充跟班的村童,回到江蘇會館。
二人因為試期已近,到了會館還在燈下狠狠念了幾篇《東萊博議》方才安寢。一宵 無話。到了次日,江氏弟兄既擾了劉理台,少不得找個地方還席。真是光陰似箭,日月 如梭,看看已是殘冬。汪老二鎮日鬧得發昏,把帶來捐官的銀子用得七零八落。
到了除夕,除掉罄其所有開銷各帳,還托尹仁借了一千銀子,才能夠敷衍過去。到 了新年逛琉璃廠,逛白雲觀,自有一番熱鬧。暫且把江老二按下不表。
且說江氏弟兄在客中過了新年,轉瞬之間,各路大幫舉子紛紛趕到。緊接著裡頭傳 出日子,各省舉人在保和殿復試。這保和殿是輕易不開的,地下的草長到丈把多長,殿 上黑洞洞的一無所有,所有的是鳥雀糞、蝙蝠屎、蜘蛛網三樣東西而已。
復試前幾日,方才有人上去打掃打掃。江氏弟兄於銀錢二字最為吝嗇,他們本是寒 士,無怪其然。又捨不得出個二兩、三兩借住文淵閱、實錄館那些所在,只得坐著半夜 ,趕城進來:穿了衣裳,戴了帽子,手裡提著考籃,背上背著可以支起來寫字的小桌子 。兩個人一步高一步低,和著幾個同鄉同年進了中直門,到保和殿門口。
其時雞才叫過了一遍。看看天明尚早。雖是春天天氣,然而北地嚴寒,刮面尖風吹 過來令人膽戰心驚。大家商量著,蹲在房簷下,把背上的桌子卸了,把手裡的考籃放了 ,趁著油紙燈籠圍在一處吃潮煙。那江澄波更是不濟事,守到四更多天氣,他也不管什 麼,頭靠在滾肚石獅子上就鼾然入夢了。大家也有些倦意,隨便打個盹兒。
將及五更,遠遠聽見吆喝之聲,角門上點起燈籠,原來是監試的王大臣來了。少時 天色微微透亮,各處靴聲踢禿,都是些復試老爺們。這裡大家揩揩眼睛,把東西收拾好 了,湊上淘去。良久,良久,角門上方才點名。點一名發一本卷子,進去一個。江文波 叫江之氵矣,江澄波叫江之涯,二人聽得叫著自己名字,上去接了卷子,魚貫而入。
江澄波是個近視眼,走路本來不甚仔細,接卷子的時候又摘去了近光鏡子拿在手裡 ,不想接了卷子剛剛跨步,不曉哪一位在他背上推了一下。他鏡子拿不住,掉在地下, 拍撻一響,想是碎了。他正嚷著,蘇拉吆喝著:「勒汗勒積!」原來「勒汗勒積」是滿 洲話,叫做禁止喧嘩,他也不懂。有個同年是老內行,拉了他一把說:「這地方可鬧不 得!」江澄波無奈,如瞎子失了盲杖一般,一步一步摸進去。等到上保和殿的台階,那 台階有一百多層,比房子還高。大家正上得五六層,只聽見「嘩啷」一聲,不由得大吃 一驚。
欲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